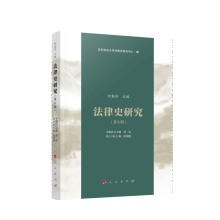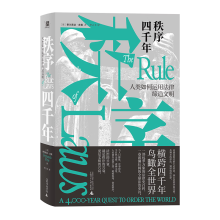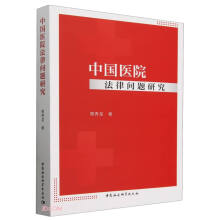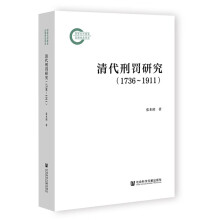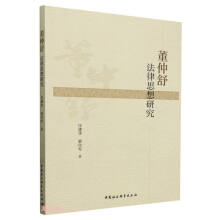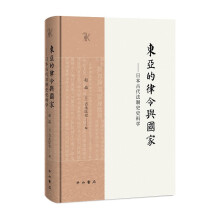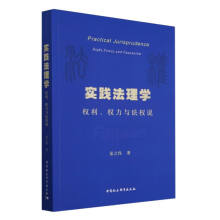《唐代涉僧法律问题研究》:
如在唐代佛教事务管理的行政规定方面,以《道僧格》中的“任僧纲”条、“私度”条以及僧籍、度牒制度为例。时至唐代,佛教事务管理已然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严耀中所言,寺院僧侣一旦隶属于行政,行政体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僧尼行为的价值取向。②唐代的佛教僧人彻底地完成了从“方外之宾”到“治内之民”的转变,因此佛教僧官僧籍制度也就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中的一部分,而不再是特别事宜。相比佛教事务管理的其他方面,行政方面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究其原因乃与历任帝王的宗教政策有着极大的关联。但总的来说,即使除去武宗“会昌法难”的特殊情况,王权对教权的干涉也是明显的日益深入。
在刑事法律制度方面,以《道僧格》中的“非寺院”条、“准格律”条、“观玄象”条以及“卜相凶吉”条等刑法类条文在唐代社会中的实践情况为例,从中可以看到唐朝设置这些条文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佛教势力过大而形成社会动乱,也就是上文所言的“试图将僧尼的活动局限于寺院中的例行修持”。但佛教的俗讲、卜相凶吉、疗疾等行为均已深入到社会生活当中,此时的佛教已经与民俗相结合,成为民众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此时的寺院也成为社会大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之一。所以唐朝的这种“将僧尼的活动局限于寺院中的例行修持”的想法并不成功。最终官府对僧人与此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只能以结果为导向,因人因事而论。
再从宗教戒律方面的法律制约来看,如《道僧格》中的“和合婚姻”条、“饮酒”条等宗教法规定及其相关法律实践。《道僧格》中宗教戒律的这一部分正是《道僧格》的核心与精髓,正是因为这一部分的存在,才使得《道僧格》这一“冷门”的格典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但同时也能看到,唐朝的这种将宗教律法吸收进国家制定法体系的尝试并不成功,除了佛教戒律中与法律伦理中相符合的部分被严格执行(如僧人犯奸罪问题)外,其他部分的执行程度并不乐观。原因在于“戒律”的设置从根本上讲是为了保证信仰的“纯洁性”,这就意味着戒律从本质上就具备着一定的变通性。这种变通尤其体现在唐代中后期禅宗流行之后,禅宗的流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僧人的戒律观,信仰的“纯洁性”不再以守戒为象征,反而以“破戒”表达对信仰“高级理解”,这就使得《道僧格》中宗教法的部分在实践中极为尴尬。此外官员个人的宗教态度也使得此类规定的法律实践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以上种种因素最终导致了这些条文薄弱的实效性。
对佛教僧人身份服制方面的法律规定也是如此,如《道僧格》中的“三宝物”条、“禁毁谤”条、“行路相隐”条的法律实践情况。严耀中曾经提到,如果是国家加于寺庙僧尼头上的规范是“硬性”的,那么中国的法律条文和司法精神对佛教戒律和约束思想的影响则是潜移默化与“软性”的。①这种分析放在《道僧格》对僧尼身份法之相关规定上,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国家对佛教僧尼在身份服制上的约束与佛教僧团自身向中国传统伦理的靠拢是相辅相成的,佛教僧团自身的这种靠拢实际上乃是文化碰撞大背景下的一种自然调节。这尤其表现在“致拜君亲”的问题上,佛教僧人虽然极尽所能地抵抗形式上的“致拜”,但从文化层面而言,忠孝思想依然被佛教教理教义所吸收,因此该问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伪问题”。
还有财产法方面的“不得私蓄”条,唐代寺院经济之发达已为学界所共识,此外唐代还明确规定了僧尼授田,这与《道僧格》中的“不得私蓄”条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乃是“寺院常住”与“僧尼私产”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的概念所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