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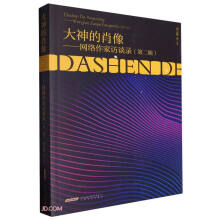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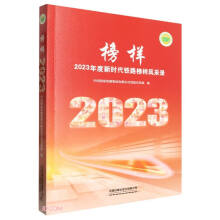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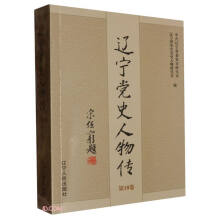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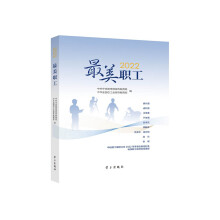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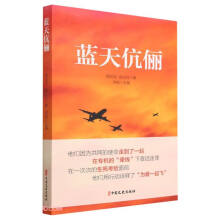
本书记录了二十多位20世纪知识界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如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哈伊姆•魏茨曼、奥尔德斯•赫胥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等。这些人,伯林都很熟悉,他以自然天成的幽默感、睿智轻松的语言、不带恶意的勃勃兴致讲述了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个人印象。书中还详细描写了1945年和1956年在苏联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感人至深。加上“彼时,我在何处”和“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等回顾性文章,读来又像一本印象式的自传,引人入胜。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
一
在距今已经久远的1928年,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国诗人兼评论家出了一本探讨英语散文写作艺术的书。[1]该书写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时代,爱德华时代辉煌的假象,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造势豪言,都已经幻灭,作者不免对简洁之美加以赞赏。如果说简洁的散文常常枯燥单调,它起码是诚实的。如果说简洁的散文有时文笔生涩、文采匮乏、读之索然,它起码传达出了真实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它能抵御所有诱惑中最难以抵御的诱惑:自命不凡,自吹自擂,搭建起徒有其表的门面,以光滑假象欺骗世人,或精雕细琢掩饰可怕的内在空虚。
时代背景已经够清楚的了:是在利顿·斯特雷奇[2]以自己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名流说话是怎样的言不由衷或脑子都是一盆浆糊,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风尚之后不久;是在伯特兰·罗素揭去了19世纪那些形而上学大家的面纱,让人们看清他们编出了一个巨大骗局,蒙骗了一代又一代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之后;是在凯恩斯成功地抨击了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在凡尔赛的种种愚行和丑行之后。这是一个修辞和雄辩挨骂的时代,骂它们是在粉饰文学和道德上的那些伪君子,那些冒充内行的无耻之徒,败坏了艺术品位,令求真寻理名声扫地,最严重的时候,还会激发邪恶,并把一个容易轻信的世界引向灾难。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下,前文说到的那位评论家才很巧妙也很有眼光地,解释了他为什么更欣赏那个可怜的鱼贩子万泽蒂对塞耶法官说的最后那句记录在案的话—一个大老粗临死前口中迸出来的不合语法却感人的破碎语言,而不太欣赏当时大众广为阅读的名家美文。
他选了一个人作为名家的例子,此人尤其被视为该评论家极为推崇的谦恭、正直、博爱,尊重他人感受、个人自由、私人情感等品质的死敌,还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浪漫主义人生观赫赫有名却不受信任的倡导者、恃强凌弱的军国主义者、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和记者、一个致力于培育私德的世界中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此人便是时任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抛出“雄辩须具备这三个必要条件—首先,要有一个恰当的题目;其次,要有一颗激情澎湃的拳拳之心;最后,还要有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之后,作者引用丘吉尔大约四年前问世的《世界危机》第一部中的一句话透彻阐述了其观点,进而指出:“这样的雄辩是假的,因为它矫揉造作……意象陈旧,隐喻生硬。整个段落散发着虚假的戏剧气氛……连珠炮般的修辞祈使句。”接着,他说丘吉尔的散文夸夸其谈、堆砌辞藻、故作雄辩、慷慨激昂,是过分的“夸耀自我”而非“弘扬主题”的产物。总之是连根带叶都一通狠批。
在一个不仅是修辞,甚至连庄重的雄辩都似乎成了无法容忍的矫饰的年代,这个观点很受年轻人的青睐,因为他们只求对赤裸裸的真相有个大概的了解,凡看似多余的东西,他们都深恶痛绝。丘吉尔的评论者是在为战后一代人代言,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当时方兴未艾的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心理病症,虽然政府当局执意地转移开视线,但目光最不敏锐的文艺评论家也看得一清二楚。到处弥漫着不满、敌对、不安的情绪;那么多恢弘气派结出的是太苦的苦果,因而留下了一个痛恨恢宏风格的传统。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们认为,他们有权将一个出卖了他们的无情时代的装饰之物剥去。
然而,这位苛刻的评论家及其读者大错特错了。他们斥之为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纸糊的东西其实很坚实,是那位作者赖以表达他那豪迈、多彩、有时太过单纯甚至天真,但始终很真诚的人生观的自然方式。这位评论家所看到的只是一幅难以令人信服,破绽百出的模仿之作,但这是一个错觉。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一种富有灵感的复兴尝试,尽管也许是无意识的。它之所以逆当代思想和情感潮流而行,纯粹是因为它是对从吉本、约翰逊博士开始,一直延续到皮考克和麦考莱的正式的英语表达方式的刻意回归,是丘吉尔为了表达自己独到观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合成武器。在凄凉萧条的20世纪20年代,对于帝国主义时代那些敏感而又世故的追随者来说,这观念太过鲜艳、宏大、生动,太不稳定,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既复杂又脆弱,无法也肯定不愿意欣赏白昼之光,因为它毁掉了那么多他们曾经信任和热爱的东西。这令评论家及其支持者心有余悸,但他们对原因的分析则不能服人。
他们当然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价值尺度,但把丘吉尔的散文视如虚假的幌子,弃如空洞的赝品,则是一种错误。复兴不能说就是虚假。比方说,哥特复兴,即便有些怀旧,也代表了对生活的一种热情态度。有些复兴的例子也许显得古怪,但复兴源于更深沉的情感,较之后来的某些单薄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可说的东西要多得多。哥特复兴的倡导者通过回归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过去而获得了解放,这一事实丝毫不会有损他们的名声或成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受到平庸世界的摆设的束缚,只有感觉到自己是站在舞台上的演员时才有生气,得以解放,第一次畅所欲言,结果发现有很多话要说。还有一些人,他们只有穿着制服、甲胄或戏装才能施展自如,只有戴上某种眼镜才能看见东西,只有在对他们来说较为正式化的场合才能有大无畏的表现,他们把生活看成一出戏,他们和别人都得听从指派,念上几句台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上次战争就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例子):当生活发生戏剧性变化,平日里惯于退缩的人上了战场,也会有奇迹般的英勇表现;而且只要制服不脱,生活永远是战场,他们就有可能会一往无前,继续猛打猛冲。
这种对框架体系的需求不是“逃跑主义”,不虚伪,也不异常,更不是失调的标志。它往往是一种取决于人的性格中最强烈的一个心理要素的经验观:其表现形式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力量或原则之间的简单斗争—真假之间、善恶之间、对错之间、个人的正直与各种诱惑与腐败之间(如本文所讨论的这位评论家的情况)的斗争,也可以是人们眼中永久的东西与昙花一现的东西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生命之力与死亡之力之间、艺术信仰与其假想敌(政客、牧师或市侩)之间的斗争。生活可以透过多个窗口来看,没有哪个窗口就必然清晰或者必然模糊,比其他窗口的扭曲程度更小或更大一些。既然我们的思维工具主要是语词,那么语词就必然有铠甲的属性。约翰逊博士的风格在丘吉尔《最光辉的时刻》一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纵情于严肃的玩笑时尤其如此,这种风格本身在其自己的时代就是一件攻防武器。无需敏锐的心理洞察能力就能看出,一个像约翰逊博士一样易受伤害的人,一个在精神上属于上个世纪的人,为什么总需要这一武器。
……
一本令人着迷的文集……很难想出另一位如此精辟、如此有趣,而又如此完全不带恶意的作家。
——安东尼·斯托尔,《旁观者》
伯林可爱的特点就是,他能欣赏那么多完全不同的人,能为我们描绘他们每一位,并且看到他们的核心特点。
——玛丽·沃诺克,《听众》
这是一本非常感人和严肃的书,也是一本脍炙人口的书。
——理查德·科布,《卫报》
与哈姆雷特相同的是,他[伯林]也惊叹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杰作,与哈姆雷特不同的是,他喜欢人类。
——诺尔·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