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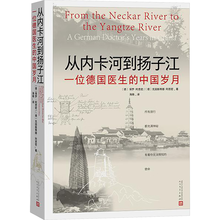







先是在当下失去她,然后又在过往里失去她。《生命的层级》是巴恩斯纪念爱妻的私密之作,追忆生命中的爱与失去。本书入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年度好书。
你把以前从未放在一起的两个人放在一起。有时候,这就像你首次将一个氢气球绑到热气球上:你是想要先坠毁后焚烧,还是先焚烧后坠毁?但是,有时候,这是行得通的,而且某些新的东西会应运而生,而世界也为之一变。然后,在某个节点,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其中一人迟早会被命运夺走。而被夺走的总是大于原先的总和。在数学上这或许解释不通,但在情感上是可能的。
阿布•克莱亚战役之后,“目及之处,尸横遍野”。战死的阿拉伯人“死无葬身之地”,但他们无不被一一查验。每位死者的手臂上都缠了一条皮质手环,手环上有一篇马赫迪撰写的祷文。他信誓旦旦地对士兵说,祷文可将英国人的子弹化为乌有。爱赋予我们一种相似的情感:信念和所向披靡。有时候,或许往往,那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在枪林弹雨中躲闪,就像莎拉宣称她可站在两滴雨点之间不被淋湿。然而,总有暗箭突然射向脖颈。因为,每一个爱的故事,都是一曲潜在的悲伤恋歌。
在人生早期,世人被粗略地分为两大类:有过性生活者和尚无性生活者。后来,划分为尝过爱的滋味者和未尝过爱的滋味者。再后来—至少,如果我们够幸运(或者,不妨说,很倒霉)—划分为已忍受悲痛者和尚未忍受悲痛者。这些划分是绝对的,就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
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我们相遇时,我三十二岁;她去世时,我六十二岁。这三十年,她是我的生之所在,心之所向。她讨厌衰老。年方二十,她就认为自己活不过四十。我却满心憧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时光变慢,我们一起追忆往事。我能想象自己无微不至照顾她,我甚至能够—但其实没有—想象自己像纳达尔那样,学着温柔护士的模样,轻抚她鬓角的白霜(她憎恶这种依赖,于我而言却无关紧要)。恰恰相反,从夏至秋,从确诊到她离世,在这短短三十七天中,伴随我的是焦虑、惊慌、担忧与恐惧。我尽力不回避,始终直面这一切。结果呢,我既癫狂又清醒。多少个夜晚,当我离开医院,我发现自己在幽怨地凝视着公交车上归家的上班族。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懒懒散散、无知无觉地坐在那儿,一个个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情,而这世界即将改变了呀?!
死亡,一件既平庸又独特的事情,我们都不擅长应对。我们已不再能够赋予它更多的内涵。正如E. M.福斯特所言,“一场死亡也许可以说明自身,但并不能阐释另一个人的死亡”。因此,哀痛转而变得难以想象:不仅是它的时长和深度,还有它的色调和纹理,它的幻象和谵妄,它的屡屡发威。还有它起初的震荡:你突然跌落冰冷的北海,浑身却只有一件滑稽的软木浮力夹克助你求生。
而你一旦被卷入这一新现实,就根本无法未雨绸缪。我就认识一个人,她心想—或希冀—她可以做到。她的丈夫罹患癌症已久,几近奄奄一息;她很务实,提前就要了一份书单,收集了有关亲人亡故的所有经典文章。但是,当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一切准备都功亏一篑。“那一刻”:你感觉已熬过了漫漫数月,但经查验证明,原来不过才寥寥几天。
很多年,不经意间,我会忆起一位女作家在比她年长的丈夫去世后写下的文字。在经历悲痛的过程中,她承认,灵魂深处有个声音在隐隐地向她透露真相:“我自由了。”当轮到我时,我清楚记得这一点,我害怕那提词者的低声细语听起来像是一种辜负。但是,此音,此语,都没有听到。一份悲伤并不能启迪另一份悲伤。
《生命的层级》是巴恩斯以文字为白色大理石为妻子筑造的泰姬陵。
——《卫报》
《生命的层级》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一个人的离世,以个体事件阐释失去、痛楚、悼念以及巴恩斯称为“孤独”问题的普遍意义。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布克奖评委称巴恩斯为“心灵的魔术师”,《生命的层级》再次证明了这句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