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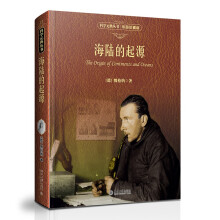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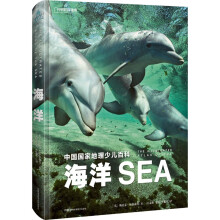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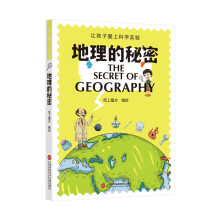



在被强劲的西南风阻退两次之后,女王陛下的十炮双桅军舰“小猎犬号”,在皇家海军菲茨罗伊船长的指挥下,终于在1831年12月27日从德文港(Devonpor)启航。这次远航的目的是完成金船长(Captain King)于1826年至1830年开始的对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的考察工作;然后考察智利和秘鲁的海岸线及太平洋里的一些岛屿;并进行一系列环绕地球的精确时计测量。
1月6日,我们到达特尼里弗(Teneriffe),但被禁止登陆,因为当地人怕我们将霍乱带上岸。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太阳从大加那利岛(Grand Canary island)崎岖不平的轮廓后面升起,一瞬间照亮了特尼里弗的顶峰,峰顶下仍然笼罩在又轻又白的云彩之中。这是行将经历的许多令人愉快的日子中的第一个,让人永远难忘。1832年1月16日,我们停泊在圣地亚哥岛(St.Jago)的普拉亚港(Porto Praya)。圣地亚哥是佛得角群岛(Cape de Verd archipelago)的主岛。
从海上望过去,普拉亚港一带非常荒凉。远古火山的焚烧、热带阳光的灼烤,使得大多数地方的土壤都不利于植被生长。整个地区是阶梯似一级级升高的台地,间或穿插一些断垣的锥形山丘,地平线处有一系列更巍峨但高低不一的群山环绕。透过这种气候特有的朦胧观看,景色十分迷人。当然,只有刚刚从海上来,第一次走进椰子树丛中,除了自己的快乐外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这么讲。一般认为该岛很乏味,但对任何只习惯英国风景的人而言,不毛之地蕴有一种独特的风采,有植被反而会被破坏掉。一块块宽广的熔岩平原之上,几乎找不到一片绿叶;但成群的山羊,还有少许的牛,竟能赖以为生。降雨不多,但每年极短时间内,会有瓢泼大雨,浅浅的植被旋即布满每一个缝隙之中,很快凋谢后,就成为动物们赖以生存的牧草。但此时已经整整一年没下雨了。海岛最初被发现时,普拉亚港周围都是树木。鲁莽的破坏使得这里如同圣赫勒拿岛(St.Helena)和一些加那利岛屿一样,几乎完全荒芜。宽阔平坦的山谷,除了每个雨季中有几天变成河道外,长满了光秃无叶的灌木树丛。这些山谷中没有什么动物。最常见的是翠鸟(Dacelo Iagoensis),它温顺地停在蓖麻的枝叉上,时而箭一样地冲向蚱蜢或蜥蜴。翠鸟色彩鲜艳,但没有欧洲种那么漂亮。在飞行姿势、动作和栖居地(通常是在最干涸的山谷中)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异。
有一天,两名军官和我骑马去了大里贝拉(Ribeira Grande),普拉亚港往东几英里的一个村子。一路都是同样的暗褐色景象。只有在圣马丁(St.Martin)山谷里,一条非常小的溪流滋养出一溜令人眼睛一亮的繁茂植被。骑行一小时后,我们到达大里贝拉,意外地看见一个破败的大堡垒和教堂。这个小镇,在港口住满人之前,是海岛的中心;如今它看起来令人伤感但非常漂亮。我们找到一个黑人神父做导游,一个曾参加过半岛战争的西班牙人当翻译,跟随他们参观了一系列的建筑,重点是一个老教堂。岛上的总督和地方长官都埋在这里。有的墓碑上刻着十六世纪的日期。
纹饰是唯一让我们联想起欧洲的东西。方形庭院的一面是教堂或礼拜堂,院中间长了一大丛香蕉。另一面是一个医院,住了十来个可怜兮兮的病人。
我们回到小旅店吃午餐。一大群墨黑的男女老少赶来看我们。我们的这些新同伴快乐无比,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引来开怀大笑。离开小镇前,我们参观了大教堂。它显得不如那个小一些的老教堂富裕,但拥有一架小管风琴,能发出些不和谐的怪声。我们给了黑牧师几个先令,西班牙翻译拍拍他的头,爽朗地说,他相信肤色无关紧要。我们随即快马加鞭,赶回普拉亚港。
有一天,我们骑马去了靠近岛中心的圣多明戈村(St.Domingo)。在途经的一个小平原上,看见一些发育不良的金合欢树,树顶因为持续的信风吹打,弯成奇怪的形状,甚至与树干成直角。树枝的方位恰好是东北方和西南方:这些天然风标显然标记了信风风力的主要方向。行走在这么贫瘠的土壤上留不下脚印,道路不明显,结果我们迷了路,走到富恩特斯(Fuentes)去了。到了以后才发现走错了,但我们后来也很高兴。富恩特斯是一个美丽的村庄,有一条小溪。这里的一切似乎都生机勃勃的,除了按说最应该富足的居民们。赤身裸体、面容憔悴的黑孩子们,背着半人高的大捆木柴。
在富恩特斯附近,我们看到了一大群珍珠鸡,有五六十只。它们特别警觉,不让人接近。它们逃离我们时,像九月雨天里的鹧鸪,头翘得高高地跑;若被穷追不舍,就马上飞起来。
因为岛上其他地方都很惨淡,圣多明戈风景之美出乎意料。这个村庄坐落在一个山谷脚下,周围是分层熔岩形成的锯齿状峭壁。黑色的岩石与清澈见底的小溪两岸的亮绿色植被相映生辉。恰逢节日,村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返回的路上,我们追上了一群黑人女孩,大约二十多个,穿戴极有品位。彩色头巾和大披肩衬托出黑皮肤和雪白的长裙。当我们快接近时,她们突然都转过身来,把披肩铺在地上,唱起了一首热情奔放的歌,手在大腿上打拍子。我们扔给她们一些葡萄牙钱币,她们尖叫着、笑着收下了。马蹄绝尘处,歌声更响亮了。
一天早晨,景色格外清晰:远山在深蓝色的云层上轮廓分明。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根据在英国看到类似景色的经验,我以为空气中湿度已经饱和。但事实竟然完全相反。湿度计显示,气温与露点的温差有29.6度。这个差值比我前几天早晨观察到的几乎加倍。这种极度干燥的天气,伴随闪电不断。这样的天气,能见度却如此高,应该是很罕见的吧?
大多数时候,这里天气朦胧。这是因为有不易觉察的微小尘埃降落所致。我们发现天文仪器都被轻微磨损了。停泊普拉亚港的前一天早上,我收集了一小袋这种棕色粉尘。粉尘可能是被桅杆头的风标上的沙网从风中过滤下来的。莱尔先生(Mr. Lyell)也给了我四包落在另一条船上的粉尘,该船当时在离这些岛屿往北几百英里处。埃伦伯格教授发现,这种粉尘主要由有硅质外壳的滴虫和植物的硅质组织构成。在我送给他的五个小包中,他已鉴定出不少于67种不同的生物!这些滴虫,除了两个海洋种类外,都是生活在淡水里的。我还找到了至少15个关于粉尘落入大西洋远航船只的报道。根据粉尘下落时的风向和发生的时间,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落尘都来自非洲,因为落尘总是发生在刮哈麦丹风的那几个月内,而且已知这种燥风会把尘土扬起卷入大气层中。但奇怪的是,尽管埃伦伯格教授认识很多非洲特有的滴虫,但在我给他的粉尘中,他居然没有找到一种,反而发现了两种他迄今知道只生活在南美洲的滴虫。降落的尘埃量很大,可以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弄脏,眼睛也被它弄得难受,有的船甚至因为能见度太差冲到岸上去了。它经常落在距非洲海岸几百甚至千里以外的船上,波及点的南北跨度达1600英里之遥。我惊讶地发现,在离陆地300英里的船上收集的粉尘里,有大于千分之一平方英寸的颗粒混迹于更细微的尘埃之中。知道这个事实后,我们就不会为隐花植物的小孢子可以扩散而感到奇怪了。那些孢子轻得多小得多。
这座岛的地质是其自然史中最有趣的部分。驶入港口时,可以看见在海崖这一面有一条沿海几英里,高出水面45英尺左右的完全水平的白色堤坝。仔细观察会发现,该白色岩层主要由钙质物构成,里面嵌入了无数的贝壳。其中大多数、甚至所有的贝类仍然生活在邻近的海岸上。堤坝位于古老的火山岩石之上,上面还覆盖了一层玄武岩,大概熔岩流入大海时,正好遭遇下面的白色贝壳海床。熔岩的炙热导致的变化很有意思,它把其覆盖的那一层易碎的贝壳有的部分变成了石灰石晶体,有的部分则变成了密实的斑点石。石灰石碰上熔岩流下层的渣状物时,则被转变成一簇簇精美的辐射状的纤维束,宛如霰石。熔岩流形成一级级的缓坡平原,渐入岛内,最高处正是最初熔化的岩浆流的起源地。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圣地亚哥岛并没有任何火山活动的迹象。岛上众多红色灰烬形成的山峰顶上,连一个火山坑的形状都难得一见。然而,最新的熔岩流在海岸边清晰可辨,它们形成比旧的熔岩流更低但延伸得更远的断崖。所以,悬崖的高度可以用来估算熔岩流发生的大致年代。
在我们逗留期间,我对一些海洋动物的习性做了观察。有一种大个的海蛞蝓(Aplysia)很常见。它长约五英寸,土黄色的身体上有紫色脉线。下部或脚的部分的两侧都有宽宽的膜,可能有时用来透气,激起水流流过背鳃即肺部。它吃长在泥泞浅水里的石块上的细嫩海草。我在它的胃里找到几粒小石子,跟鸟的砂囊一般。这种海蛞蝓被骚扰时,会射出一股很细的紫红色液体,把周围一英尺范围内的水搅浑。除了这个防御办法,它还可以分泌一种刺鼻的液体布满全身,碰上会有尖锐螫痛的感觉,类似被僧帽水母(也叫葡萄牙军舰水母)所刺。
尤其让我兴致勃勃的是好几次观察到章鱼(即墨鱼)的习性。这些动物虽然在潮退后的水坑里常见,却不容易抓到。靠其长胳膊和吸盘,它们能把自己拽进很窄的缝隙里。一旦这样固定在里面,需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再把它们揪出来。有时,它们猛地一窜,尾巴先动,像箭一般迅速地从水坑的一边冲到另一边,并同时射出暗栗褐色的墨汁把水染黑。这些动物还有一种不寻常的变色龙般的变色方法来逃避跟踪。它们似乎可以随地方不同而变换身体的颜色。在深水中,它们一般呈棕紫色;但放在地上或浅水里,这暗色调就转为一种黄绿色。仔细观察,其肤色是法国灰,但上面有无数微小的亮黄斑点:前者的强度会变化,后者则可以忽隐忽现,轮流变换。色调变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产生的:从风信子红到栗褐色之间的各个色调的云团,在身体里不断地移动。任何部位,一经轻微电击,就几乎完全变黑;用针在它的皮肤上刮,也能产生类似效果,但程度稍轻一些。这些云团,或称红晕,据说是由含各种不同颜色液体的囊泡交替膨胀和收缩产生的。
这种章鱼无论是在游泳时,还是伏在水底时都会显示它的变色龙本事。有一条章鱼让我乐坏了。它似乎完全知道我在观察它,于是用尽各种招数藏身。它先一动不动地趴着,然后悄悄地挪一两英寸,就像猫抓老鼠那样;有时候还变一变颜色。就这样慢慢移动,终于挪到了更深一点的地方。突然它一闪身就没了,只留下一道墨黑的轨迹把它爬进去的洞口掩盖起来。
寻找海洋动物时,我的头大约离岩石海岸两英尺以上,却不止一次被一股水柱招呼,还能听见随之而来的很轻但刺耳的摩擦声。起初我想不出这是什么东西,但后来发现,还是这种章鱼。虽然躲在洞孔里,如此却让我轻而易举就找到它了。章鱼能喷水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它肯定还能用身体下侧的导管或吸管瞄准。这种动物抬头有一定困难,放在地上爬行时很不自如。我抓了一只放在船舱里,发现它在黑暗中还闪一点磷光。
《小猎犬号航海记》是达尔文青年时期的成名作,生动地记述了改变他人生轨迹、历时五年的环球科考之旅,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也一直是青少年的*佳读物。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中科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张弥曼
我很欣赏本书译者陈红的文字,简洁而优美,配以这部传世经典,恰似琴瑟相依,读来心旷神怡,如同享受了一次大自然之壮美与知识之乐趣的沐浴。
——中科院院士,周忠和
尽管《物种起源》是达尔文最负盛名的扛鼎之作,《小猎犬号航海记》却是青年达尔文的成名之作,以至于达尔文晚年提起此书时,依然津津乐道、情有独钟,自称是他著述生涯喜得的“头胎”(the first born),在其所有著作中视为至爱而自珍。当译林出版社寻找《小猎犬号航海记》译者时,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陈红……她译笔的灵秀与精湛,读者自可评判。
——古生物学家、著名科普作家,苗德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