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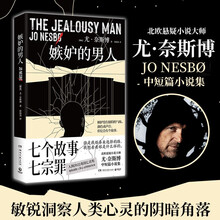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部中篇小说是阿乙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名十九岁青年的自述,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伤害与逃亡之旅,让人一口气不停歇地直奔向前,迫切想知道他为什么犯罪。
故事基于一件真实的案件而写。
小说已被译成英语、法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韩语出版。
智利作家拉蒙•迪亚斯•埃特罗维奇(Ramón Díaz Eterovic)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空虚、罪恶和孤独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部小说中的三大要素——主人公生存的空虚使他将当下和未来都视为毫无意义的时空;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他蓄意杀人;逃亡开始后,孤独如影相随。阿乙将小说平衡地构建在此三大要素之上,其故事情节的发展引人入胜,精准地刻画出了主人公的心理肖像,见证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末日。”
书的封画创作者陈青琳说:“阖上书页后,如同小说书名《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意象,感受到更强烈与自我对话的意愿。”
重版此书,作者阿乙对之进行了部分修订。
看似普通的一天开始,只是十九岁的“我”正在为杀掉自己唯1的朋友做准备,“我”把她引诱到家里,取其性命,案发地血流成河。就这样,“我”成为社会焦点,一场以“我”为主角的猫鼠游戏就此展开。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通过对一件“无由”谋杀案的描述,展现虚无者的可怕心理。伦敦大学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认为作者阿乙在技术上对一起黑暗事件做出了完美无瑕的描述。
一
今天,我去买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反而欲盖弥彰,后来挑上一副普通平光眼镜,似乎就好很多,它一点也不招摇,看见我的人们又准会以为我是一名由来已久的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相信戴眼镜的人。我还买来透明胶带。我试着将自己的一只手缠绕起来,要用很久才能将之剥离。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添置衣服这一项,然而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来岁,身形矮小,脸很黑,脸颊上长着一颗蓝黑色的痣,其上生长一根细毛。刚有一位顾客对她的容貌嘲笑有加。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行使自己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就大为后悔。这是一双没办法再低三下四的眼睛,我走到哪,那目光就追随到哪。我正要走,听见她叫唤我为叔。她凄惨地说:“外边一千多元的我这里卖几百元。一样的货,都在我这儿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这些能招徕顾客的话她背诵起来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将它扔下。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门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遗憾地跟出来。这时路前方走来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身穿西服,脚踏锃光瓦亮的皮鞋,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未料她低呼道:“有啊,怎么没有?”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时瞅着我,生怕我走掉。她果然都替我找齐,只是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搂着衣服去试衣,出来后照镜子,见有发蜡,问:“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用指头揩出好大一坨,将头发梳得乌亮,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岁吧。”
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惊惶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出来后,我将新衣丢下,注视她有六七秒(她真是难看啊),问:“多少钱?”她顿住,然后整个人几乎痉挛一下。她很快便从计算器那里算出结果。“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元,只收五百八十元。”她说。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元,否则一点利润也没有。”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看着她那仍然不曾消退的一脸的兴奋,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两百元。”
“本都不够,叔。”
“两百元。”
“你要是真心诚意,四百元拿走。”
“我只有两百元。”
“两百元买走四样东西,这样的生意做不起。你要是买哪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掉。身后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分明听见两个她在她心内吵架,一个她急着要出来叫住我,另一个她则认为还应该等等,这时谁做出主动的姿态就意味着谁必须让步。我接着往下走,就在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听见她喊:“等等,两百元给你。”我回头,看见她表现得十分懊恼,简直是在气急败坏地朝我招手,另一只手则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袋子。我挥手回应,然而并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我身上只剩十元,也许还有几个镚子儿。
下午六时三十分,我回到学院的家属院,何老儿恰好也回来。院子内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学院的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他们四肢并拢,笔直地站着。
我远远跟随何老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打开自家的门。屋内啥都没有。有时候我真盼望在打开门的同时,有些什么窃贼扑上来。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消磨眼下的时间。据说为用掉过于充足的时间,劳改犯总是刻苦地去学习各种知识,以至出狱后变成经常被人请教的能人。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卫生间,努力想着某位女生,想她们搔首弄姿的模样,然而什么也想不出。尽管如此,我还是完成射精。
随后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得找点事情干。我走进书房,揿亮灯,在角落里有一台不设密码锁的军绿色老式保险柜。上边盖着一层防尘罩,堆放着一樽插着塑料玫瑰的瓷瓶、一捆《大众电影》杂志、一个花盆以及一只纸箱。移开这些东西后,我找出自己钥匙中差不多大小的那把,插进保险柜锁芯,缓慢试探。接着我揿灭灯。黑暗使人专注,并且变得富有耐心。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字画、玉器、美元、子弹壳等玩意儿。
我想当叔母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一定会愤怒到极点,然而又不敢声张。这是她应得的。我们家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奔叔叔,是两家必须完成的交易的一部分。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是成绩更好的爸爸做出让步,供养叔叔读大学,而自己在煤窑把肺搞坏了。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叔母,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本地人,便觉得我们全都是在沾她的光。妈妈将我送到省城时,拿出老家的土特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嘛,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说:“我妈妈可是比你能挣钱。”我住进家属院时,叔母和叔叔还没搬走。不得不说,那是我极为难熬的一段岁月。拘谨,压抑,羞愧,脸色总是发红。我无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无法判断她是否如意。记得有一次,她突然说:“难道说我连电视都不让你看了?”我这才想起,因为恐惧于她的指责,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开过电视。她总是反复地擦地,墩布擦过后,还要跪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吱吱地响。我曾想去与她相识的人那儿打听,以判断她的洁癖是过去就有,还是从我出现后才有的。
现在她住在另一校区的家属楼,漫长地装修一间复式公寓。叔叔去地方上挂职已久。我一个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自由,现在却觉得自由不过尔尔,总是有一股发霉的味道。时间太富余,我没办法用完。
我捏着钥匙柄,轻轻且反复地去转动它,整个人沉浸于其中。这时从走廊处传来脚步声,停下,又听见钥匙在叮当作响,来者找准一把,粗鲁地插进锁芯,防盗门应声而开。有人回来,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突然意识到什么,往外扯它,可它的齿部却卡死在里边。仓促间我不慎将钥匙扭断。叔母开第二道门时,我凭感觉罩好防尘罩,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杂志呀瓷瓶呀花盆啊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重新布置一次。放花盆时我的手剧烈颤抖,差点让它掉下来。
书房——也可以说是库房——的门是虚掩的。
叔母对着客厅和卧室观望一会儿,来到书房,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着数字:四十四、四十五。她推开门,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推开门,让客厅的光漏进来。
“俯卧撑。”我喘着气说。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揿亮灯,示意我离开,于是我站起来,拍打手掌上的灰尘。她捉起瓷瓶看看,将它扔进纸箱。也许她要去查看那台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她这时却回过头来,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么?”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脸颊的皮都在跳,然而人还是僵立在原地。
“出去。”
直到她再次下达命令,我才走出来。在客厅,我痛苦地等她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什么回来?”她说。
“不用。”我说。
她似乎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头,然而还是开门离去。
读《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像坐过山车,请抓好扶手,不要松,做好旅程结束才能放松的准备。
——《洛杉矶书评》
有趣的是,除了故事的精准性和节奏之外,《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也为我们剥开了一个备受折磨却空虚的灵魂,这个灵魂存在于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当中。同时,它让我们感受到刻印在所有人类行为背面的凛凛寒意。
——何塞•玛利亚•盖尔本苏(José María Guelbenzu),西班牙《国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