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我一个苏州
苏州是江南大于整体的局部。它占有江南不多的美,但患有江南不少的病。
江南是被江南文人搞小的
我并不是太喜欢江南,无论是词,还是物,都有点软,有点粉。江南是奢侈的。许多地方都超出我的理解力—— 一个在江南长大的苏州人的理解力。
我眼中的江南很小,我常常把江南看成苏州。苏州是江南大于整体的局部。它占有江南不多的美,但患有江南不少的病。从人性上谈论苏州,大概如此。
软和粉,其实也不错。只是江南的软和粉,是有点软有点粉,还到不了极致。软但不是水性,粉但不是铅华,小家子气,风土人情都缺乏大手笔。江南的小家子气,不是说江南山水,说的是江南文人——江南是被江南文人搞小的。尤其是近几十年。
“一星如月看多时”的黄景仁,北上京师,除了谋生,更是求活,以求大一点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大了,个人才好找活路。谋生像是物质保证,求活像是精神需要。郁达夫对黄景仁情有独钟,看来不仅仅隔代知己,也是地理上的逃脱。精神需要往往是从地理上的逃脱开始。隋朝开皇年间,大英雄杨素把苏州从伍子胥圈定的城池中逃脱出去,在七子山下建造新城,不能光认为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杨素的艺术气质箭在弦上,到他子孙杨凝式手上终于射出,百步穿杨的时候,就是洛阳纸贵。杨凝式洛阳书壁,恰好五代——江南也就是在五代发迹从而名声大振。俗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五代人的说法。
只是我在苏州生活,却从没有身居天堂的感觉。我一直寻找这种感觉,结果是别人的天堂,他们的城市。我在苏州是这种感觉,现在离开,还是这种感觉。我已难以和苏州达成和解,尽管应该把苏州和苏州人区别对待。可以这样说,迄今为至,我受到的全部滋养来自苏州,我受到的全部伤害来自苏州人。耿耿于怀未免斤斤计较,想一笑了之,真能一笑了之的话,我又觉得自己不是在韬光养晦,就是装孙子。这可能是一回事。韬光养晦在坊间的说法就是装孙子。困难的是装孙子的到底是老子在装呢还是儿子在装——这是装小;还是曾孙子在装呢还是末代孙子在装——这是装大。既不能装孙子,又不想耿耿于怀,就只得把一口恶气吐在苏州身上。我是因为苏州人才不能和苏州和解的,这话听上去自负。我当然自负,否则也就难以求活。自负是山穷水尽时的精神需要,与途穷而哭一样。我的宗教是艺术,我的信仰是自负。
苏州已被有知识没文化有客套没教养的空气污染。
我一写苏州,就会心态失衡语无伦次。
也正因为如此,苏州让我保持现实感:你还将受到侮辱,你还将受到损害,你还将受到不公正,只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正因为如此,我要感谢苏州——它让我尽可能地一意孤行独来独往。
我现在生活在一个远离苏州的地方,感觉日子安逸了,就回苏州。苏州至今倒还不失那样的能力,可以把我搞得乱七八糟。在中国,我看非传统安全因素文学作品在狭隘的小城出现,它的发生方式似乎更可靠些。
以上文字断断续续,像是提纲。写到凌晨,撑不住了,就睡。现在起床续写,想补充、发挥,兴致全无。
……一回苏州,我就忍不住为周围的人事生气,以致失去写散文的心境——
赔我一个苏州!
苏州被搞成这么个样子,哪里还有一点古城味道?
赔我一个苏州!
人不能死而复活,城市也是如此。杜牧之的江南,范石湖的苏州,在前三十年还依稀可见,在近十年被破坏得比任何时期都要厉害。现代化的代价如此之大,盲目、急功近利、割断记忆……最后必将得不偿失。其实这不是现代化问题,普遍的浮躁、当事人和决策者的贪婪、刚愎自用、草率、市民的麻木、地方名流心怀叵测的顺从,用偷梁换柱的现代化覆盖不能再生的文物性。江南的一些城市具有文物性……
这段文字没有完成,以致终不能完成了。
粉黛记
年代长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老照片上的白色。年代短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会劈面的白色、会扑鼻的白色。……雨痕逶迤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从初夏的水稻田里路过的白色。树荫下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把梨子皮削掉的白色。藤影中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咬出的白色。
粉墙黛瓦:“苏州色”。
粉墙好看,黛瓦当然也好看。粉墙有种在底层的感觉,平起平坐,与我辈亲切。黛瓦看起来就没有粉墙方便,要抬头,或者俯视。在苏州不能老抬头,苏州人讲礼,老抬头会让人觉得骄傲。以至我于黛瓦终究讲不上,对粉墙似乎还能一说。
年代的长短,位置的阴阳,雨痕,树荫,藤影,人家的气息,夜与昼,都会使视线之内的粉墙和而不同,尽管它们都是白的,却白得千变万化。我走过一些地方,也见过一些粉墙,比较起来,还是苏州的粉墙最幻。这种幻,除了“年代的长短,位置的阴阳”等等因素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忘记——这就是黛瓦。
黛瓦在粉墙头上不露声色地一压,粉墙的白就白得从容、谦虚、内敛、谨慎。
多年以来,我想我也是一堵粉墙,只是该压在我头上的黛瓦还在窑里烧,所以我就难免不从容不谦虚不内敛不谨慎了。前面说过,年代的长短,位置的阴阳,雨痕,树荫,藤影,人家的气息,夜与昼,都会使视线之内的粉墙和而不同,现在再往下说。年代长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老照片上的白色:从发黄的情境中挺身而出的那小块白色。年代短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会劈面的白色、会扑鼻的白色。位置受阴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纯棉织品上纤维的白色。位置向阳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在飞机上看云的白色。雨痕逶迤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从初夏的水稻田里路过的白色。树荫下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把梨子皮削掉的白色。藤影中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咬出的白色。人家的气息里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吃早饭时候的热气腾腾的豆腐浆的白色。夜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阁楼上的白色。而昼的粉墙,它的白色像是刚被发明的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虽说粉墙只有一种颜色:白色,它却一点也不单调,甚至比苏州姜思序堂生产的国画颜料更为神奇,传统品种也就是花青、藤黄、胭脂、朱砂、石青、石绿、赭石、银朱这几种,但一到画家手下,就调合得出奇花异卉灵岩怪石:
绯红,用银朱、紫花合。
桃红,用银朱、胭脂合。
肉红,用粉为主,入胭脂合。
柏绿,用枝条绿入漆绿合。
黑绿,用漆绿入螺青合。
柳绿,用枝条绿入槐花合。
官绿即枝条绿。
鸭绿,用枝条绿入高漆合。
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
鹅黄,用粉入槐花合。
柳黄,用粉入三绿标,并少藤黄合。
砖褐,用粉入烟合。
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黄标合。
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黄、檀子合。
鹰背褐,用粉入檀子、烟墨、土黄合。
银褐,用粉入藤黄合。
珠子褐,用粉入藤黄、胭脂合。
藕丝褐,用粉入螺青、胭脂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黄、檀子合。
茶褐,用土黄为主,入漆绿、烟墨、槐花合。
麝香褐,用土黄、檀子入烟墨合。
檀褐,用土黄入紫花合。
山谷褐,用粉入土黄标合。
枯竹褐,用粉、土黄入檀子一点合。
湖水褐,用粉入三绿合。
葱白褐,用粉入三绿标合。
黎褐,用粉入土黄、银朱合。
秋茶褐,用土黄、三绿入槐花合。
鼠毛褐,用土黄粉入墨合。
葡萄褐,用粉入三绿、紫花合。
丁香褐,用肉红为主,入少槐花合。
我把王绎《调合服饰器用颜色》略抄一下。“用”粉墙“入”黛瓦,苏州它也早已“合”了。“用粉入螺青、胭脂合”,是“藕丝褐”,苏州是根藕丝,藕断丝不断,回忆是苏州最好的画家,最好的颜料商。
文章到这里本没什么好写,但我略抄之后心生喜欢,简直像抄《花间词》,觉得内心里的那个读者还没走,就再写几句。王绎生活在元末明初,擅长画人物肖像,著有《写像秘诀》。《写像秘诀》这书我没见到,《调合服饰器用颜色》一节从《六如画谱》抄出。
《六如画谱》据说为唐伯虎所辑,我是不相信的,太杂乱无章,而且不仅仅审度不精,还辑录了让人不高兴的《画说》,“三字一句,鄙俚不堪”。
我倒没有不高兴,托名荆浩所作《画说》,在我看来,很可能是民间画工口诀,其中让人不明白的句子,无非是行话。就像苏州姜思序堂传人薛庚耀总结制作国画颜料的“十大要诀”,比如“矿渣淘清植物泡够”,这我还有点明白,因为制作国画颜料的原材料不是矿物就是植物,而像“倾倒有度眼到手到”,我不是颜料行的,自然就不知所云。既然写到姜思序堂,我就又要往下写了,内心里的那个读者想走就走,我不管。我家住彩香新村,以前上班的地方在桃花坞,从石路走,总会路过姜思序堂,姜思序堂门面隔壁是近水台(一家经营面食的百年老店)。这是姜思序堂的新门面?姜思序堂原先开在东中市都亭桥一带。东中市都亭桥一带我比较熟悉,马路一侧有不少小吃店,有家小吃店的“馄饨千金”是我朋友的学生,他们师生恋了一阵,我朋友曾经请我去考察她。记得“馄饨千金”十分乖巧,脸蛋宛如一只白壳鸡蛋。写远了。还是回到姜思序堂。那几年我每次从姜思序堂门前路过,对这家老字号心怀好感。后来它不知怎么地卖起涂料、油漆,店堂里摆满邋里邋遢的塑料桶、铁皮桶。后来再路过,连姜思序堂也不见了。偶然听人说起,姜思序堂已搬到虎丘附近。是不是如此,我不清楚。最近又听说姜思序堂被外来商户抢注,市面上兜售的“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实在与姜思序堂没有关系。这么一个著名作坊,当今苏州……[此处删去愤激之词若干,大家理解(老车自注)。]
我从没用过姜思序堂国画颜料,我在等着自己哪一天画得好一些后再用,否则会觉得暴殄天物。平日我用上海产快餐似的锡管国画颜料。更多时候,我什么颜料也不用,宣纸之上只拿些水墨散步,这是我在怀旧北京的粉黛,有人说好,我就卖给他。
门泊东吴万里船
以前的诗人,不来苏州荡,不写苏州诗,就算不上出道
如果要编一本苏州诗选,一般会从陆机《吴趋行》开始。这个头开得好,陆机在钟嵘《诗品》中名列上品,有“才高词赡”和“举体华美”之誉。他的《吴趋行》:
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座并清听,听我歌吴趋。
这个头也开得好,有幽默感,让我想起快板书:
打竹板,竹板响,听我把××讲一讲。
我疑心民间艺人就是从陆机那里学来的。我们总是强调文人向民间学习,其实民间也从文人那里学到不少。江西的民间说唱艺人常常一开口就是黄庭坚诗句,连听者也浑然不觉。
《吴趋行》里有一句“土风清且嘉”,就是顾禄《清嘉录》的由来。
说实话,《吴趋行》写得并不好,不如陆机有关北方的作品。而李白《乌栖曲》在李白所有诗歌中,也是一首好诗。李白对“吴王宫里醉西施”的神往,也是对中国文化青春期的赞美。有人以为这首诗暗含针砭,因为《乌栖曲》第一句是“姑苏台上乌栖时”。其实乌鸦起码在宋朝之前,并不被人认为不祥之物,甚至还能报喜,像喜鹊似的。古琴曲《乌夜啼》为我们存留个中消息,而下面将说到的张籍就有一首《乌夜啼引》,中有“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云云,也是例子。
张继《枫桥夜泊》太有名了,以致顾颉刚这么说:“山东王子容来游寒山寺,大懊恼,谓受诗人之骗”。《枫桥夜泊》有欧阳修的公案,老生常谈。现代文学的废名大师也有他的看法,一般人不留意,我摘抄几段:
我在一篇小文里讲到“夜半钟声到客船”,据我的解释是说夜半钟声之下客船到了。据大家的意思是说夜半的钟声传到客人的耳朵。我的解法,是本着我读这诗时的直觉,我不觉得张继是说寒山寺夜半的钟声传到他正在愁眠着的船上,只仿佛觉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两句诗写夜泊写得很好,因此这一首《枫桥夜泊》我也仅喜欢这两句。我曾翻阅《古唐诗合解》,诗解里将“到客船”也是作客船到了解,据说这个客船乃不是“张继夜泊之舟”,是枫桥这个船埠别的客船都到了,其时张继盖正在他的船上“欲睡亦不能睡”的光景,此点我亦不肯同意,私意确是认为是张继的船。
废名写来有些饶舌,我也懒得摘抄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关于“夜半钟声到客船”》。
我小时候,第一次得到的拓片,就是俞樾所书《枫桥夜泊》刻石。我不喜欢俞樾的字,有福气,没有才气。我喜欢宁愿一辈子都没有福气,但到老也不缺才气。功力另当别论,因为每个时代对功夫的理解有所不同,而对福气与才气的理解却变化不大。
张籍有《送从弟戴玄往苏州》一诗,中有“夜月红柑树,秋风白藕花”一联,不错,尽管所写之景放到哪里几乎都能通行,并没有苏州特色,但还是不错。网师园里有座濯缨水阁,这“濯缨”两个字本来就露,加上郑板桥“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对联,就显得滑稽。“曾三”指曾参“吾日三省吾身”,“颜四”指颜回“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禹寸陶分”则出于《晋书·陶侃》,陶侃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所以陶侃一有闲暇,就把百十来只大缸早晨搬到门外,晚上又搬回去。有人奇怪,他说,人的生活优逸了,以后恐怕不胜人事。陶侃没错,这副对联也很好,只是这样入世的热情放在苏州园林里,就与园林精神不符,贴到政府办公室比较合适。“夜月红柑树,秋风白藕花”一联,挂在濯缨水阁,才差不多。
有句话“苏州刺史例能诗”,因为唐朝的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都做过苏州刺史,这三人不但是诗人,还是大诗人。韦应物更被称作了“韦苏州”。他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的最后四句: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
一般说来官样文章都面目可憎,韦应物这几句话也是官样文章,却说得动听。这就是大诗人。由此可见,苏州很早就两手硬,不但经济硬,文化更硬得像童子卵。
白居易“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正月三日闲行》),写的确是苏州。在我看来,还应该是苏州今后重建的规划。
“苏州刺史例能诗”这句话,出自刘禹锡酬答白居易的一首诗,白居易正任苏州刺史,全诗(《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如下:
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二八城门开道路,五千兵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骑过虹桥剑戟随。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
这首诗气魄不小,只是不像写苏州,倒像在演京戏,“二八城门开道路”是《空城计》,“五千兵马引旌旗”是《定军山》,“水通山寺笙歌去”是《白蛇传》,“骑过虹桥剑戟随”是《穆桂英挂帅》。或者说他写的也是苏州,只不过不是唐朝的苏州,而是春秋时期的苏州,写这首诗时的刘禹锡还没到苏州,但肯定把《吴越春秋》先学习了,这首诗有后汉赵晔《吴越春秋》的笔法。什么笔法?小说家笔法。
以前的诗人,不来苏州荡,不写苏州诗,就算不上出道,杜甫没来过苏州,着急啊,凑出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后,心情方好起来。
苏州女人和苏州男人
嫁给苏州男人,等于嫁四个人
“女士请,女士先请!”
苏州女士先请。
苏州并没有多少绝色佳人,苏州女人的容貌水准普遍较高,在这么个水准中,要出落拔尖得出类拔萃,就不容易。不像有些地方女人的容貌水准普遍较低,那地方往往出美女,因为不均匀,好处尽往一两个女人身上奔跑而去。
苏州也并没有多少难看女人,除容貌的“均贫富”外,苏州水土也颇有大师风度,像陆游,写作近一万首诗,质量大致衡稳,不见明显落差。
苏州女人十分能干,其实中国女人都十分能干,只听说家道在男人手上衰落,没听说女人把家败掉。不但能干,还常常能干好。范仲淹这个家族,不就由一个寡妇一手拉扯而大?
旧社会的苏州女人像全中国女人一样。后来妇女解放,苏州女人的解放程度在中国就首屈一指了,首屈一指或许说不上,那也名列前茅。解放得早,负担就少,再加上苏州气候又不寒冷,又产绫罗绸缎,所以苏州女人一般都能轻装上阵。用个比喻,苏州女人像是轻骑;再用个比喻,苏州女人像是空心菜,朝气蓬勃,骨头都鲜嫩碧绿。
旧社会的苏州女人只得在家里嗑瓜子,一嗑两爿,客堂地上瓜子壳黑压压一片,不露一点白。不但旧社会的苏州女人在家里嗑瓜子,旧社会的中国女人大多数也是在家里嗑瓜子,能把瓜子嗑得如此身怀绝技,也只有苏州女人,她们虽说是解厌气,专注程度却并不小于刺绣,嗑嗑嗑,并且更带着烈火干柴般的热情。所以一旦得到解放,苏州女人的能量也就可想而知。有一种气概在男人身上不见得美观,在女人眼里就看得到它的魅力。苏州女人既能让男人闲着,又能让男人不闲着,男人不闲着的时候因为爱苏州女人,闲着的时候也因为爱苏州女人。苏州女人能让人爱,俗话说“讨人欢喜”,尤其是讨外地男人欢喜,这是苏州女人的特长。
上面说到瓜子,从一个城市瓜子销售量上,能看出这个城市妇女解放程度。据说现在采芝斋“玫瑰西瓜子”“奶油西瓜子”卖不大动,我听了心里高兴,说明苏州女人都在工作,没有因为解放得早,就停止进步,没有让男人豢养,而一些大城市却刮起一股闲妇之风,苏州女人不受影响,可以在妇女解放史上继续记上一笔。
苏州女人瓜子是不嗑了,但喝起酒。起码是我认识的一些苏州女文学艺术家都会喝酒。我走过几个地方,从没见过有像苏州女人把酒喝得那么豪爽的。京城里的几位资深编辑说,苏州女人喝酒太厉害了,拿着一大杯烧酒,说敬敬你,一口就干。关键是喝酒之后,还能工作。
我对苏州女人所知甚少,写不好。
快,跟上!苏州男人。
天生男女共一处。写完苏州女人,我就该写写苏州男人。但我知道我也写不好。因为我就是苏州男人,不识庐山真面目。
我自认为我这几年在北京,是做了点宣传苏州地方文化工作的,主要向北方姑娘推销苏州男人。“推销”这个词用得不好,好像苏州男人娶不到老婆。应该说成“介绍”。我这几年一有机会,就向北方姑娘介绍苏州男人。
我说“吃在成都,嫁在苏州”,一个姑娘家能找个苏州男人做老公,那是前世积德,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
有的北方姑娘被我吊起胃口,就问苏州男人好在哪里?
我一般在介绍苏州男人之前,捎带着先介绍介绍苏州,然后再说男人。
我说苏州男人……现在要用文字记录,反而不知从何写起。那就写到哪里是哪里,缘分吧。
我说嫁给苏州男人的好处之一,可以免除后顾之忧,苏州男人都会下厨房,你不让他下,他对你急。如果嫁给其他地方的男人,他要等你回家后由你烧煮喂食,而嫁给苏州男人,你一回家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汤汤水水,比上饭店还舒服,关键是你根本不用操心买单。嫁给苏州男人,等于嫁四个人,你嫁了一个苏州男人,你还嫁了一个饭店老板、一个饭店厨师和一个饭店服务员。嫁一个不容易,一下同时嫁四个,已经稳赚,最起码绝不赔本。
我说嫁给苏州男人的好处之一,男人酗酒是北方的社会问题,苏州男人不酗酒,许多苏州男人别说让他酗酒,就是种卡介苗,酒精在他胳膊上那么一擦,他就醉倒。所以苏州医院里的麻醉师常常闲着没事,根本不用他去麻醉,只要叫护士给准备动手术的苏州男人看一眼碘酒,就确保他人事不省。你想想不喝酒能省多少钱?嫁给苏州男人,等于嫁给煤气罐——他为你做饭,等于嫁给储蓄罐——他为你存钱。
我说嫁给苏州男人的好处之一,他决不会对老婆动手,内心里还盼望着被老婆痛揍,如果他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情,你不打他,他还会愤愤不平,老婆怎么如此残忍,都不打我了?苏州男人怕老婆,是苏州的伟大传统,这点我已于《在苏州梦游》里说过,这里就不多说。我要说的是嫁给苏州男人,等于嫁给出气筒。苏州男人不但对家庭做出贡献,也对社会做出贡献,女人们的气都能打一处去,社会也就稳定一半。嫁给苏州男人,往大处说,等于嫁给和谐社会。
我说嫁给苏州男人的好处之一,苏州男人普遍温柔,有刺绣的、唱昆曲的、说书的,这样的男人不温柔,谁温柔?嫁给苏州男人,等于嫁给一床鸭绒被。
诸如此类。我通常一次只说一条,因为北方姑娘都很聪明,是真聪明,不是苏州姑娘小聪明,她们自然会依此类推。也有将信将疑的北方姑娘,相比苏州姑娘,她们的确实在,她们说每个产品总有它不尽人意的地方,那么他们的缺点呢?
我说这得让我想想。有一次真让我给想起,我说苏州男人的缺点,就是他不能解开上装,给孩子喂奶。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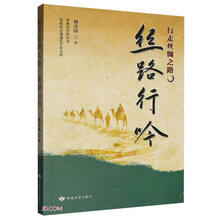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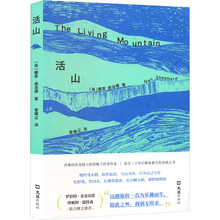



——著名编剧 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