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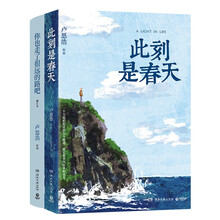








这是托尔斯泰在1910年,也是他在世的最后一年写下的日记,从1910年1月2日写起,到11月3日结束,共计266篇。
82岁的托尔斯泰,记述日常、家人、不能避免的开心或者不开心,还有他计划了40年的离家出走,"为要使自己一辈子的最后几天在孤独和静寂当中过去而隐遁于世外"。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给妻子留书一封,而后离家。路途中生病,11月7日,逝世于离家出走途中的一个小车站。
一月四日
悲哀、忧郁,但心情柔和。想要哭出声来。做祷告。再把《梦》加以修改。不晓得改得好不好,但觉得非改不可。这是一项必要的工作。收到许多信,可是回复得不多。独自骑马散心,非常悲哀。对于周遭的事物,觉得毫不相干。想到我们对待同这世界上的非宗教的人们的关系,那完全是跟对待其他动物的关系一样。也能爱他们,怜悯他们,但不能在精神上跟他们打交道。这样的关系,唤起了不良的情感。他们不能理解,而以那种无知和自信,就把理性和真理弄得暧昧不清,对真理与善加以反驳,诱发了不良的情感。
我不能好好地表达出来,但我正感到:为要不至于破坏对这些人的爱情,在自己内心,实在有建立与他们的特殊关系的必要。
去吃饭。上帝呵,赐给我力量,让我不会忘记自己只是您的仆人,而跟您同在!
夜里,塞略且跟我畅谈朵霍波尔教徒移居的情形。化装舞会又开始了!阅读无聊的书,玩牌。
一月五日
醒来得很早。在院子里散步。看到那些在自己家里劳作着的婢仆们,越发感到苦痛。跟这些人相对的时候,我就努力想要在心中祈祷。可爱的尼古拉爱夫(托翁挚友,一位翻译家)和亚布利科索夫(托翁一位亲戚)来了。很高兴。跟尼古拉爱夫谈了许多话。亚布利科索夫充满着精神生活。收到许多信。给希米特及沙马拉的回教徒写回信。此外,什么事都没有做。不断地觉得烦闷。
去吃饭。夜里,把《梦》念给大家听。从各方面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但我以为是一部好作品。玩牌。不断地觉得烦闷、羞耻。
一月六日
来了很多信,但引得起兴趣的不多。影片给送来了。把《梦》和《贫困》稍加整理。决定就这样邮寄给柴尔特科夫。写着写着,就停止下来,又从头写起,把写好的东西加以种种斟酌:这种做法,一般地来说,是必要的。
昨天,来了一个犹太人,说是要我把人生的意义极简单地加以叙述。我所说的,一切都不对,都是主观的;我们所需要的,乃是站在"进化"的基础上面的客观的东西。死啃住所谓有学问的人,都是可惊的鲁钝和糊涂。
什么也没有写。不断地感到羞耻,心里烦闷。跟昨天相比较,越发来得厉害。和朵香一同骑马散心。沙夏跟索尼亚吵架(沙夏是托翁最小的女儿,索尼亚是托翁夫人,母女从来就合不来,时常争吵,尤以一九一〇年为甚)。去吃饭。
夜里,看无聊的电影。玩牌。
一月七日
精神状态稍显良好。已不再感到无法挽救的忧郁,但对民众觉得无限的羞耻。就在这种羞耻状态中了结我的一生吗?上帝呵,救救我吧。我知道在我的内心进行着怎样的变化。请在我的内心里面,给以力量吧。
早上睡懒觉。乘雪车到科兹洛夫卡去。拍电影。无聊。许多乞讨的和请求布施的。尽是些无聊的事情。在路上碰到三个穿得很好的男子。他们也求布施。我忘记了上帝,予以拒绝。而当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跟那些来自皮洛哥哇的可怜的年轻人畅谈,他们都穿着破旧衣裳。碰到沙夏和娃利亚。又是电影。
……
读了几封来信。当中有一封使我颇觉不快,它用了确信而夸张的口气,要我为基督教普及事业而捐助五百卢布。什么也不想写。已经一点钟了……
只是无所事事。跟朵香一同骑马散心。爱哥尔·巴威洛维齐(一位居住在邻村的农民)从耶生卡来访,为农民们收买土地的事情。吃饭。可爱的布里金(一位跟托翁居住的很近且亲密的朋友)来。和欧尔斯费爱夫作别。又是电影。无聊。
我完全没有力气了。是应该休息的时候了吧。
一月/1
二月/29
三月/47
四月/73
五月/99
六月/127
七月/160
八月/186
九月/214
十月/243
十一月/279
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高尔基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列宁
伯爵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集叙事诗、历史小说和和风习志之大成的独树一帜的作品。发表以后,它在公众的心目中就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屠格涅夫
《安娜·卡列宁娜》作为一部应运而生的艺术作品是十全十美的,而且当代欧洲文学没有一部类似的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复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托尔斯泰那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的灵魂的目光,比在他别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这束目光在每个灵魂中看到神的存在。--罗曼·罗兰
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我感觉他的确了不起。他笔下的妓女玛斯洛娃给人一种圣洁之感,而我们有些小说的所谓"圣洁女性"形象却给人卑琐之感。这就看出大师与普通作家之间的差别了。--迟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