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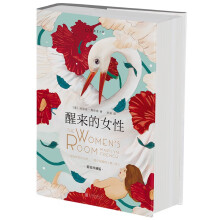



无论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奥野健男评《斜阳》
太宰治的一生,都在书写真实与自由,毁灭与重生。
战争时期鼓吹的“真理”,在战后分崩离析,太宰治以小说《斜阳》道出了年轻人心中的困惑。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从文本中读出年轻人永恒不变的迷惘:“思想?谎言。主义?谎言。理想?谎言。诚实,真理,纯粹,全都是谎言。”
被笼罩在阴影下,不疯魔不成活,才是消极艺术家太宰治对现实的积极抵抗。
在双子座太宰治身上,玩世不恭与真诚锐利、懦弱无赖与温柔善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像极了每个想要努力活得闪光又力不从心的我们。
太宰治的小说并非只有颓丧与叛逆,还有永不妥协的思想与意志。百年之后的少年,捧起太宰治的作品,仍能获得其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斜阳》写于太宰治去世前一年、1947年6月前后。战后身为贵族出身的母亲家道中落,为生计跟女儿和子被迫搬到伊豆的小别墅度日。不久后被征入伍的弟弟直治从南洋回来,每日跟着作家上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与此同时,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在一儿一女的陪伴下与世长辞。母亲死后,和子决定无牵无挂地为爱革命,前去与仰慕的上原求爱。次日清晨,弟弟直治于家中自杀,留下一纸遗书描述自己的痛楚与过去……《斜阳》写作于日本战败之后,全书充满了战争的伤痛和成长的痛楚,是日本著名的成长小说之一,深受年轻读者喜爱。
一
早晨,母亲在餐厅里舀了一勺汤,“嘶”地啜了进去。
“啊。”她低低地惊叫了一声。
“是头发吗?”
汤里想必混进什么不洁的东西了吧,我想。
“不是。”
母亲若无其事地又舀了一勺汤,动作灵巧地送进嘴里,然后转头望着厨房窗外盛开的山樱花,就那么侧着脸,动作灵巧地舀一勺汤,从小小的嘴唇缝里灌了进去。“动作灵巧”这种形容,对母亲来说一点儿也不夸张。母亲的进食方法,和妇女杂志上介绍的完全不一样。弟弟直治有一次一边喝酒一边对我这个姐姐说过这样的话:
“有了爵位,不等于就是贵族。没有爵位的人,也有的自然具有贵族高雅的品德。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有人光有爵位,根本谈不上贵族,仅仅接近于贱民。像岩岛(直治举出同学伯爵的名字)那种人,给人的感觉甚至比新宿的游廓拉客的鸡头还要下贱,不是吗?最近,柳井(弟弟又举出同学子爵家次子的名字)的哥哥结婚,婚礼上瞧他那副德行,穿着无尾晚礼服,有必要穿那种衣服吗?这还不算,在致辞的时候,那家伙一个劲儿运用敬语表达法,实在令人作呕。摆阔和高雅根本沾不上边儿,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本乡一带有很多挂着高级宅第的牌子,实际上,大部分华族可以说都是高等乞丐。真正的贵族,是不会像岩岛那般摆臭架子的。就拿我们家来说,真正的贵族,喏,就像妈妈这样,那才是真的,有些地方谁也比不上。”
就说喝汤的方式,要是我们,总是稍微俯身在盘子上,横拿着汤匙舀起汤,就那么横着送到嘴边。而母亲却是用左手手指轻轻扶着餐桌的边缘,不必弯着上身,俨然仰着脸,也不看一下汤盘,横着捏起汤匙,然后再将汤匙转过来同嘴唇构成直角,用汤匙的尖端把汤汁从双唇之间灌进去,简直就像飞燕展翅,鲜明地轻轻一闪。就这样,她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之中,轻快地操纵汤匙,就像小鸟翻动着羽翼,既不会洒下一滴汤水,也听不到一点儿吮汤和盘子的碰撞声。这种进食方式也许并不符合正规礼法,但在我眼里,显得非常可爱,使人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贵族做派。事实上,比起俯伏着身子横着汤匙喝汤,还是微微仰起上半身,使汤汁顺着匙尖儿流进嘴里为好。而且,奇妙的是这种进食法显得汤汁更加香醇。然而,我属于直治所说的那种高等乞丐,不能像母亲那样动作轻巧地操动汤匙,没办法,只好照老样子俯伏在盘子上,运用所谓合乎正式礼法的那种死气沉沉的进食方法。
不只是喝汤,母亲的进食方法大都不合乎礼法。上肉菜时,她先用刀叉全部分切成小块,然后扔下刀子,将叉子换在右手拿着,一块一块地用叉子刺着,慢条斯理地享用。遇到带骨的鸡肉,我们为了不使盘子发出响声,煞费苦心地从鸡骨上切肉时,母亲却用指尖儿倏地撮起鸡骨头,用嘴将骨头和肉分离开来。那副野蛮的动作,一旦出自母亲的手,不仅显得可爱,而且看上去很性感。到底是真贵族,就是与众不同啊!不光是带骨的鸡肉,午餐时的火腿和香肠等菜肴,母亲有时也用手指尖儿灵巧地撮着吃。
“饭团子为什么那么好吃,知道吗?因为是用人的手指尖儿捏成的缘故啊。”
她曾经这样说。
用手拿着吃的确很香,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像我这样的高等乞丐,学也学不像,只能是越学越觉得像个真正的乞丐,所以还是坚忍住了。
弟弟也说他比不上母亲,我也切实觉得学母亲太难,有时甚至感到很绝望。有一次在西片町住宅的后院,初秋时节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和母亲坐在池畔的亭子里赏月,娘儿俩说说笑笑,谈论着狐狸出嫁和老鼠出嫁时,配备的嫁妆有什么不同。说着说着,母亲突然起身,钻进亭子旁边浓密的胡枝子花草丛里,透过粉白的花朵,伸出一张更加白净的脸孔,笑着说:
“和子呀,你猜猜看,妈妈在干什么来着?”
“在折花。”我回答。
“在撒尿呢。”她小声地笑着说。
她一点儿也未蹲下身子,我感到很惊奇。不过我们是学不上来的。我打心底里感到母亲很可爱。正说着早晨喝汤的事,话题扯远了。不过,我从最近阅读的一本书上,知道路易王朝时代的贵妇人也在宫殿的庭院或走廊的角落里小便,她们根本不当回事儿。这种毫不在乎的行为实在很好玩,我想我的母亲不就是这种贵妇人中的最后一个吗?
再回到早晨喝汤的事儿上吧,母亲“啊”的一声,我问:“是头发吗?”她回答:“不是。”
“是不是太咸了?”
早晨的汤是用美国配给的罐装青豌豆作底料,由我一手熬煮的potage 。我本来对做菜没把握,听到母亲说“不是”,心中依然犯着嘀咕,所以又叮问了一句。
“味道挺好的。”母亲认真地说。喝完汤,接着伸手捏起一个紫菜包饭团儿吃了。
我打小时候起就对早饭不感兴趣,不到十点钟肚子一点儿不饿,那时候有点汤水就好歹对付过去了。吃起东西很犯愁,先把饭团子盛在盘子里,然后用筷子戳碎,再用筷子尖儿夹起一小块儿,照着母亲喝汤的样子,使筷子和嘴巴成为直角,像喂小鸡一般塞进嘴里。当我慢慢腾腾吃着的当儿,母亲早已全都吃好了,她悄悄站起身子,背倚着朝阳辉映的墙壁,默默看着我吃饭的样子。
“和子呀,这样还是不行,早饭一定要吃得香甜才是。”
她说。
“妈妈呢?您吃饭很香吗?”
“那当然,我已经不是病人啦。”
“和子我也不是病人啊。”
“不行,不行。”
母亲凄凉地笑了,摇摇头。
我五年前害过肺病,卧床不起。不过,我明白那是娇生惯养造成的。但是母亲最近的病症使我甚为担心,这是一种很可怜的病。然而,母亲只是为我操心。
“啊。”
我不由“啊”了一声。
“怎么啦?”
母亲问道。
两人互相望着,似乎都心照不宣。我吃吃地笑了,母亲也笑了起来。
每当心里有什么难为情的事儿,又忍耐不住的时候,我就会悄悄“啊”的一声。眼下我心里突然清晰地浮现出六年前离婚的事儿,实在忍不住了,才不由“啊”地叫出声来。母亲又是怎么回事呢?母亲不会像我一样有着难以启齿的过去吧?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呢?
“妈妈刚才也想起什么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忘啦。”
“我的事吗?”
“不是。”
“直治的事?”
“对。”
说到这里,她又歪着头,说道:“也许是吧。”
弟弟直治大学中途应征入伍,去了南方的海岛,从此杳无音信。终战后依然下落不明,母亲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她说再也见不到直治了。可是我从来不需要这个“心理准备”,我想肯定还能见到弟弟。
“我虽然死心了,但喝到这么好的汤,就想起直治,心里受不住。要是对直治多疼爱些就好了。”
直治读高中时就一味迷上了文学,开始过着不良少年的生活,真不知给母亲招来多少辛苦。虽说这样,母亲依然一喝上一勺汤就想起直治,“啊”的惊叫一声。我将一口饭塞进嘴里,眼睛热辣辣的。
“没事儿,直治不会出事的。像直治这样的恶汉子是不会死的。死的都是老实、漂亮、性情和蔼的人。直治是用棍子打也打不死的。”
“看来,和子也许会早死的吧。”
母亲笑着逗弄我。
“哎呀,为什么?我是个淘气包,活到八十岁看来没问题。”
“是吗?这么说,妈妈可以活到九十岁啦。”
“嗯。”
说到这里,心里有点儿难过。恶汉长寿,漂亮的人早夭。
妈妈很漂亮,不过我希望她长寿。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快别捉弄人啦!”
说着,我的下嘴唇不住颤动,眼泪扑簌扑簌涌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