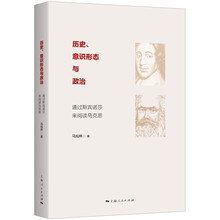实体的黑夜
请想象一下,如果再没有任何一物可想象,将是怎样的情形。那将是漫漫黑夜。连我们文化黄昏中那熟悉的光源圣堂都不再有,正是这光源,自凡尔赛的枝形烛台亮起后让宫廷中专供精英欣赏的戏剧依旧上演,在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又让民主的、普惠众生的业余休闲活动徐徐展开。可那黑夜却了无星光,黑如圣经(Starless and Bibleblack)。我,演讲人,还能聊作讲演,但已经没有任何演讲稿可念诵。你们,听众,还能聊且听之,但却无法再作任何笔录。一所大学依照尼采的听觉分析所应拥有的一切都将分崩离析。主宰一切的将是那种“对黑色的积极感知”,这是威廉·普莱尔(Wilhelm Preyer)发表于1877年的一篇开创性的生理学论文所发明的术语。
我今晚要提出的观点简单明了,用的是黑格尔那永难遗忘的名句: 当下此刻(das Jetzt)——它对应于一种位于所有历史之终结点的历史时刻——便是这黑夜。无法再想象者,于此而生,因为再无一物可想象之处,便是数据处理之所。
我们可做的,便只剩这一桩事儿,即至少标记出无可想象者的生成日期: 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可看到1989年、1945年、1806年和1295年的四次黑夜,它们之间有着多年的间隔,而这间隔的比例并非偶然地呈现为逆时序指数增长。
如今,在这1989年,宇宙空间里依统计学原理四散的剩余光亮已足以反衬出每一个黑夜。英国的宇航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借助军方缴获的军用雷达奠定了射电天文学的基础,自此以后,肉眼可见的光便成为受控制的无尽谱系中的一个特例而已。只不过,控制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电脑或者与之类似的信号处理机。所谓的非冯·诺依曼结构的机器,也即在单一运算行为中除了计算机普遍进行的加减法之外还能进行乘法和多运算域计算的计算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那“黑夜”,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在其中“所有母牛都是黑的”的黑夜,进行细致区分。即使那些由光学传感器探测到并传送给中央计算机的源数据本身缺少对比度,二维的数据处理也能重新引入边界和特征,确定它们各自的形态和可辨识性。要做到这一点,数据处理只需反复对所有单个的探测值,以叠加或递归方式,进行数学上的微分和积分运算。这样,当差分不断推出差分,便会出现无尽的棱角;当总和不断推出总和,便会出现无尽的平面。数字化的图像处理,所谓“Imaging”,就是对一个黑夜的实时分析,这黑夜不再由图像和某一语言的词汇组成,而是和今天的一切事物一样,由数字纵列组成。
但是早在1945年,在仅有的唯一一台电子计算机被运行起来,以便为英国情报部门破译德国军队无线广播用来遥控他们的坦克团和潜水艇队的那些无穷无尽的杂乱字母队列之时,夜之黑的最初轮廓就已浮现。计算机的运用并不如密码分析术那样对战争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此举促成了传感技术,而后者的源初数据便汇入了今天的数字化信息处理。
战争必须学会看,哪怕士兵们盲目。从诺曼底登陆到阿登反击战,在盟军高达20倍的空军战斗力优势完全阻止了德国坦克团在白天的行动之后,德方觉得(党卫军将领施坦因纳“Steiner”所称)“亟需一个在夜间侦察并定位目标的机器”,这个机器将首次让坦克联合队能“在夜间行军作战”。于是,武装党卫队技术部在拥有工程博士学位的奥托·施瓦本(Otto Schwab)少将——他在测量技术上的革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大放异彩——的带领下,在战争结束前夕便实现了“自力更生”: 在趋于保守的军队背后,他们从工业研究已有的仅限于基础性质的解决方案中,发展出了第一台可系列化的红外线传感器。这台传感器可以捕捉战场和敌方坦克发动机发出的肉眼不可见、但强度不一的热辐射,加入的强电流可放大热射线转瞬即逝的振幅,而恰恰是帝国邮政捐助的一台电视屏幕,则最终将这些红外线频率转化为肉眼可见的光,至此,坦克丛林面前的深夜便变透明了,透明得只有我们的剧情片电影中的美国之夜可比。“今天在东线和西线没有一台坦克是不带夜间目标定位装备的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