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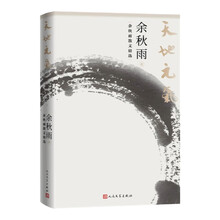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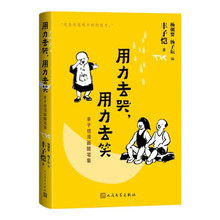



歌
二〇〇二年,我在韩国釜山大学做交换教授,常常进进出出学校边上的几家小书店。这有点奇怪,我不懂韩文,逛书店是不是装模作样?虽然不免心虚,还是去过不少次。大概是出于习惯,更因为上课之外的空闲时间很多,这也是一种消磨方式。一天傍晚,在角落里发现一本英文书,厚厚的《布罗茨基英语诗集》,眼睛一热:在一大堆看不懂的书籍中间,找到能够阅读的文字,像看见了亲人;不是母语也一点不减少亲切,因为是布罗茨基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读大学的时候,宿舍隔壁一个同学,张口闭口布罗茨基,滔滔不绝,我们干脆送他一个绰号,就叫布罗茨基。也有人心生嫉妒,又不是他一个人喜欢布罗茨基,凭什么就他赢得了这个名字。
我看看书价,犹豫来犹豫去,忍心决定不买,又暗自检讨小气。站在书店里,翻到简单的一首,A Song,默记下来,然后赶紧走回研究室,拿张纸写出。那天晚上,我想把这首诗翻译出来,可是试过几次,都觉得不对。以后几天反复试译,读读译出来的中文,声音,语气,韵律,总是不对头。不得已,只好放弃。
二〇〇八年夏天,到圣彼得堡大学开会,东方系楼下有个小花园,会前会后,会议间歇,三四天时间里都会到这里放松一下,坐一会儿,抽支烟。小花园树木掩映,四周散落很多雕像,其中我感兴趣的是,诗人勃洛克,在一个角落,那么瘦瘦长长地立着;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头像,竖在草地边上;阿赫玛托娃在树下,双臂交叉胸前,神情是忧郁,还是别的什么?说不清楚;而印象最强烈的,是布罗茨基的青铜雕像。
那是一颗头颅,放在一个破旧的旅行箱之上。
雕像就坐落在小花园一角,粗糙的水泥地,周围不是草、树和花。诗人的流亡生涯和颠簸命运一下子就凸现出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居也注意到一只旅行箱,但比起来,那只真实的旅行箱比这个青铜雕塑的破旧旅行箱,似乎要好一些。布罗茨基有一张照片,那是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他离开列宁格勒飞往维也纳,开始流亡生涯之时拍的,照片上他双腿分开,骑坐在旅行箱上。这座青铜雕像让我想起这张照片,但雕像去掉他的身体,旅行箱上只有一颗头颅,更有表现力。
而且这座雕像很小,又是直接放在平地上,你要蹲下身来,才能和它合影。
我拍照片的时候想起没有翻译出来的A Song。
二〇一五年秋天在波士顿市郊宋明炜家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送我,正是《布罗茨基英语诗集》(Joseph Brodsky, Collected Poems in Englis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和我十多年前在韩国小书店见过的版本一样。多年来,明炜断断续续送过我不少英文书,埃德蒙•威尔逊的评论,波拉尼奥的小说,曾经在明炜任教的韦尔斯利学院教过几年书的纳博科夫的残稿——写在卡片上,编排影印成书。这些,我都喜欢;一下子触动我记忆的,却是《布罗茨基英语诗集》,曾经的眼睛一热,几乎重复了一遍。前几天,就是二〇一七年最后一天,在微信朋友圈不出意外的辞旧迎新应景图文中,意外看到梁永安老师写他的心情,其中引用了几句翻译的布罗茨基诗。我马上把原诗A Song拍照,发给梁老师。
发完之后,忽然想,也许今天我可以翻译出来?再一次尝试,似乎找到了声音和语气,很快写出译稿;又发给朋友,征询意见,这儿改一个词那儿变一个韵,与一首字面简单的诗度过岁末。
第二天,元旦,下午我去思南书局。这个只有三十平米的概念店,是个“快闪店”,只存在六十天,每天邀请一位作家驻店和读者交流。我被安排在新年第一天,却已经是倒计时的最后阶段,倒数第三天。当天活动的主持人充满好意,把重点放在我刚出的诗集《在词语中间》上,其中一个环节,要我朗诵新书中的诗。当众朗诵自己的诗,对于我这样一个此前从未有过这种经验的人来说,实在太尴尬了。我随便读了一首,窘迫中忽然闪念,说,我再读一首—布罗茨基的诗。读大诗人的诗,或许能掩饰尴尬吧。于是,我朗诵了昨天译出的A Song——
歌
我希望你在这里,亲爱的,
我希望你在这里。
我希望你坐在沙发上
我坐在近前。
手帕或许是你的,
泪水或许是我的,滑到了下巴边。
也或许,当然,
正好相反。
我希望你在这里,亲爱的,
我希望你在这里。
我希望我们在我的车里,
你转换车挡。
我们会在别处发现自己,
在未知的海岸上。
或者我们去往
我们以前的地方。
我希望你在这里,亲爱的,
我希望你在这里。
我希望我对天文无知
当星星出现,
当月亮擦过水面
叹息和改变在它的睡眠中间。
我希望还是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币
拨一个电话给你。
我希望你在这里,亲爱的,
在这个半球,
当我坐在门廊,
饮一瓶啤酒。
傍晚了,太阳正在沉降;
男孩呼喊而海鸥哭叫。
遗忘有什么意义
如果跟在后面的就是死亡?
一九八九
诗后面标出年份,那一年布罗茨基四十九岁,七年后去世。写这首诗之前两年,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最后写道:“写诗的人写诗,并不是因为他指望死后的荣光,虽然他也时常希冀一首诗能比他活得更长,哪怕是稍长一些。写诗的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暗示或者干脆口授接下来的诗句。一首诗开了头,诗人通常并不知道这首诗会怎样结束,有时,写出的东西很叫人吃惊,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超出他的预期,他的思想往往比他希求的走得更远。只有在语言的未来参与进诗人的现实的时刻,才有这样的情形。……有时,借助一个词,一个韵脚,写诗的人就能出现在在他之前谁也没到过的地方,也许,他会走得比他本人所希求的更远。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此时此地
一
坐在窗口,坐在比山巅还高出一截的地方。这额外的一截,就是楼房的高度。
万山之中,有这么几座,顶部推平,建起了楼,一幢挨着一幢,连成了楼群。开发商把这叫作生态度假居住区,老百姓就信了。避暑的人拖家带口,浩浩荡荡而来。堵起车来,绝不比北京上海逊色。进了小区,你以为会安静了,哪里啊,小区里面才是人集中的地方,熙熙攘攘,声响鼎沸,又热又闹。人是最喧嚣的动物。
邀我来的朋友似乎有点抱歉,说,前年来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人,也没有这么多楼。
两年,足以改变很多了。
房地产和汽车,投资,旅游,休闲和养生,这些东西的力量,在这偏僻之地——“老虎喝水的地方”,老早土家族人这样命名——实打实地显形,强烈而突兀;不过从到此度夏的人说来,就很自然了:空气好,气温低,住在森林里面,生活方便,什么都有,林海云天,“唯独没有压力”——这一句是社区里随处可见的房产广告。
他们把城市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打包,像是整体打包,却也剔除了力图躲避的东西——说不出来的烦恼和压力,说得出来而且作为正当理由的高温酷暑——他们把生活搬进大山深处,老虎当然早就没有了,他们搬来宠物狗,甚至搬来了广场舞。晚饭后高音喇叭的声音,比在城市里更清亮,更理直气壮,山谷间的回声也更悠长。社会主义文艺是广场舞的基础和群众基因吧,伴着他们起舞的歌曲,像记忆、情感、身体的按钮,无比熟悉和亲切的魔力按钮,“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们至少有一个夏季可以永远年轻,可以唯独没有压力。
夏季一过,犹如候鸟,他们返回到真正的有压力的城市日常生活里去。这里,返回到没有人烟的寂静。
二
窗口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我随手翻开,读到这一段:
“夏季是一段绿色的、紧迫的、很多爱丢失或找回的季节。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候,就北半球的自然界而言,几乎是一下子有数十亿动物从冬眠中苏醒,还有数十亿动物从热带地区迁徙而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上演着求爱、交配和喂养下一代的狂野派对。夏季的主要任务是繁殖,而机会窗口的打开是短暂的。表面看来,夏季是嬉戏的集会,但这掩盖了潜藏的竞争和斗争,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物种的新生命而言,这个物种中都必须有平均相等数量的死亡。此外,对于大型动物而言,它们的生存需要成百上千的小型动物作为食物,这样它们才能繁衍出自己的后代。而那些小型动物也都进化出了降低被捕食概率的机制。”
这本书叫《夏日的世界》(Summer World: A Season of Bounty),是博物学家贝恩德•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对一块树林空地及周边生物的观察、记录,他特别关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文版(朱方、刘舒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封面上,印着几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米勒(Roger Miller)的歌词:“夏季,当树木和叶子变绿,红色的鸟儿歌唱,我会是蓝色(忧郁)的,因为你不接受我的爱。”
三
暑假开始,我从生活和工作的江南都市回北方老家。父母的新家在一楼,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隔出一块,种了几棵秋葵,几棵茄子,一垄生菜,一架芸豆,一架菜豆,一架黄瓜。另一边靠墙种了一长排大葱。远方来人,指着大葱,惊喜地喊:“这么多芦荟,长得真好!”
外面的草地,对着院子,有三棵年轻的柿子树,枝头已经挂上了青绿色的果实。没想到柿子树被用来做景观。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树啊,柿子也是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弟弟说,现在柿子不值钱,两三毛钱一斤,连摘的工钱都不够。柿子熟了,没人去摘。秋后,冬天,树叶落光了,红彤彤的柿子还挂在枝头,风一吹,掉下几个来,砸到地上,已经烂了。
张大千曾居巴西,他在圣保罗市郊外买了个农场,一九五四年开始造园,在此一直住到一九七〇年前后。他造园很有意思,把两千多本各色玫瑰拔除,种上梅花、芙蓉、秋海棠、牡丹、松树、竹子,有些特别的种类从日本等地运来。最特别的是,他加种了很多柿子树,柿子树有七德,他自己再加一德,所以这个园子就叫“八德园”。他没想到,后来城市人口增加,当地政府要筑水坝,建水库,供应城市用水,把这块地征收了回去。这个南美土地上的中国式园子,就慢慢拆毁了。
古久以来对柿子树的赞美,都落在那种很朴实的“德”上,所说的七德,一长寿,二多阴,三无鸟窠,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可供临书。短暂的回乡期间,我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前面的柿子树底下抽烟,是受它荫翳之德吧:夏天烈日当空,没个躲避处,抽烟更是找不到个像样的地方;树荫之下,有凉风,没有讨厌抽烟人的眼光,有丝瓜藤爬满院子的铁栅栏,大片的绿叶中间开着黄花,风大了你担心会摇落花瓣,其实一点事没有,安心抽烟好了。
四
从老家北方小城,提前一个晚上赶到机场酒店,乘第二天早班飞机,飞到一个很小的机场。这个航班十天才有一趟。走出机场打车,司机张口三百块。就这样,来到西南的群山之中,坐在山巅上的窗口。
每天看晚霞,看无穷变化的色彩和形状。这里天黑得晚,我看的时间也就很长。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详细记录过日落景象,他说日落是一场完整的演出,开始、中间和结尾,全都具备;它好像把一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战斗、胜利及失败,重演一遍,只是规模小了一点,速度放慢了一些。
楼下喧腾,生活气息浓烈。远山静默,只是存在,在那里,从远古到将来——将来,也不会所有的山顶都造起楼房吧。视野近处,楼顶上有凉亭,空阔,没有人,因而突出了框架,像在空的空间里画出的实线。暮色渐染,越来越趋浓时分,凉亭的框架柔和而肃穆。
忽然想起米沃什的诗《傍晚》,想不起全部,只是那描述傍晚景象之后,阅读者没有准备迎面撞上的一句:“谁在观赏?那怀疑自己生存的人。”
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人为什么要跑来跑去?
巴西之后,张大千迁往美国,在加州卡米尔买了一处房子,命名“可以居”,多少有点将就的意思吧。所以栖身两年后,又重新购置新住所,名“环荜庵”,重操旧路,把院子里的橡树拔了,种上从日本、越南运来的梅花;还从“八德园”运来“笔冢”碑石,立在园中。真能折腾啊,是不是?但走到哪都总有舍不掉的东西,东方树种就这样运到巴西,又运到美国;巴西的碑石,又运到加州。
张大千晚年定居台湾,又造了一个园子,“摩耶精舍”。造这个园子不用跨洋过海东西方之间运东西了吧?不。他在加州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大石头,形状似台湾岛,重达五吨,他不怕麻烦,固执地海运回来,立在后院。他说,等他死了,骨灰就埋在这块石头下面,石头就是墓碑。葬身之处,他叫作“梅丘”。
《夏日的世界》快要读完了。第十七章讲到纳米布沙漠中一种独特的植物,百岁兰,它有两片终生不脱落的叶子,常绿水嫩,寿命可达一千多年。海因里希想象,如果百岁兰能够开口,它会说:“上帝对我的仁慈和体贴超越了一切。他赋予我两片叶子,不多也不少,恰恰是我所需要的数量。他让这些叶子伴随我一生,又让我降临在这样一个适宜我的环境中,我不需要迁走,就生活在这里。他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让我无忧无虑地活上好几个世纪。这里的温度——比什么都了不起的极端夏季——非常完美。我从不中暑,大地和空气源源不断地提供食物。夜晚雾气沼沼的空气为我提供水分和二氧化碳。我简直身处天堂。他预见到每一件小事,让我的生命完整。因此,当他创造世界时,他一定把我特别记在心里。”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苏马荡
他很平和,他也很低调,但是我觉得他确实会,从他的写作也能看出来,他确实会做让你很意外的事情。在我们熟悉的新颖老师内心深处,我觉得是藏着一个很不同的新颖老师。而且这个很不同的新颖老师的存在,可能也是他多方面创作力的一个源泉。
——李敬泽(作家)
我觉得张新颖有很多碎金的东西在里面,他不会把这里面的碎金打成一件首饰,就是很有表现力的一种形状呈现出来。
——林白(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