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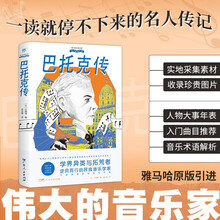





两度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日本新浪潮领军者今村昌平的野蛮生长
“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休。”这是今村昌平电影理念。纵观世界电影,很少有导演能像他那样始终手持一柄利剑,划开社会表面的光鲜外衣,剥离道德的束缚,将活生生的真实展现给世人,人性的丑陋阴暗竟也因此而变得格外动人。
能两次荣获戛纳电影金棕榈奖的导演屈指可数,但今村昌平对电影的狂热早已超过获奖本身,他甚至都没去领奖。他将这种狂热灌注于银幕之上、文字之中,坦诚而又充满力量。他更注重电影本身,曾举债千万创办日本电影学校,并鼓励年轻人勇敢而执着地追寻自己所爱。今村的电影成为世人反抗现实追寻理想的精神支柱,引领日本电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海报:

今村昌平师从小津安二郎,在电影表现手法上既有传承的一面,又突破了传统束缚,凭借先锋反叛的风格,与大岛渚等人成为日本电影新浪潮的领军者,并以《鳗鱼》和《楢山节考》两度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他善于从生、死、性这些层面出发,挖掘根植于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情色观和劣根性。无论在影像处理,还是在题材选择上,常有骇人之举,作品频频惊艳影坛。
今村昌平在本书中深刻而质朴地书写了他的电影之梦与人生达观。
永远描写好色、贪婪
我一直主张,二十一世纪是女性的世纪。从拍摄《日本昆虫记》和《赤色杀机》的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我就一直在刻画女性的坚强,这一点在最近的作品中也没有改变。
女子一直承受着充满陈规陋习的家庭、社会的摧残,然而一旦她们陡然一变释放出自己的坚强而取得自立,有时甚至能改变男人。《鳗鱼》中帮助原杀人犯正常生活的桂子、《肝脏大夫》中满不在乎地向男子提供身体的苑子、《赤桥下的暖流》中分泌出生命之水的佐惠子都是如此。
2001年,《赤桥下的暖流》在戛纳电影节上映后,法国的《解放报》称赞我为“好色老头”。我心想,我就是想要永远在对好色、贪婪的描写中追寻人类的滑稽、伟大、纯真与丑陋啊。
这部电影的原作是由共同通信社记者转为作家的边见庸所著。读了这本书使我产生兴趣的,是实际生活中是否真有女子能像佐惠子那样分泌出超常量的水。即使到了即将把它拍成电影的阶段,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向边见庸核实这件事,问得他都怕了。
电影试映一结束,一个记者模样的人到试映会场门厅里我和妻子的跟前说:
“其实我妻子就是那样的女人。我可真幸福啊。”撂下这句话,他又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听了这话,我和昭子愣得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才又都开心地感到,这个人看完这部电影好像非常高兴。
《赤桥下的暖流》之后我没有拍长篇电影,但拍了一部短片,就是《九一一事件簿•日本篇》。这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同时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后,法国作家阿莱•布瑞金发起拍摄的。他计划从世界上选出十一位导演,让每人拍出一段片长十一分九秒的超短篇电影。他从日本挑选了我,此外参加的还有法国的克劳德•勒鲁什、英国的肯•洛奇、美国的肖恩•潘、伊朗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等人。
一说起九一一事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不是受到客机撞击后毁坏的大楼,而是事发后不久到现场视察的布什总统和消防员。布什对着站在一起的消防员异常恳切似的搭话,还拍了拍他们的肩。这个场景我越看越觉得恶心,心想这真是拙劣的作秀。那些消防员看起来虽然讨厌他这番蹩脚的表演,但应酬姑且还算保持不失礼。
我也曾经见过同样的场景,见过那些呼吁“爱国”、煽动爱国心的有权者。然而,他们都是在做戏。我想拍一部电影,告诉人们“圣战”是一种何等靠不住的东西。这个灵感是从井伏鳟二《除厄特集》中的一篇文章里获得的。那其实是篇井伏鳟二按自己的理解将杜甫的诗《复愁》翻译而成的文章。我在诗句最后写上了一行字:“根本没有什么圣战!”然后将诗交给长子天愿大介,让他去写剧本。
天愿根据这篇文章,写了一个关于已经完全变成蛇的前日本兵的故事。剧中主人公由于在中国战场有过悲惨的经历,变得对人类厌恶至极,因此不再做人。主演是田口智朗,看样子他实际观察过许多蛇,研究过蛇的表情和动作。在电影最后他不使用手脚而在山中逃窜,还跳进水里游泳,吃尽了苦头。我觉得他对导演的苛刻要求完成得相当好。
这部电影的时间一开始就规定是按秒计算的,又是部相当短的电影。我只能一边拍摄,一边琢磨怎样才能提高内容密度。这部十一集的系列短片《九一一事件簿》在恐怖袭击一年后的2002年9月在日本和世界其他各国通过电视放映,又过了一年便在剧场里公映了。我拍的《日本篇》是唯一讲述与现实事件完全没有接点的故事,被放在了系列片最后一集。这恐怕是因为它与其他片子不同,只好放在最后吧。我在最后强调的“根本没有什么圣战”,制片人似乎也深深理解。
现在我手头有的,是写于十年前却因为资金筹措不到而流产的一个电影剧本,片名叫《新宿樱幻想》。这是“二战”中一个生长于新宿二丁目红灯区妓院里的早熟少年的故事,是根据辻中刚的原作《花街少年》改编的。
在和石堂淑朗一起写剧本的时候,作为“导演说明”,我写了以下这些东西:
“二战”完全是连战连败。
前线自不必说,即便是后方的国民也被煽动起来,
受尽欺骗,忍受着生活的贫困和物资短缺,
明明吃了败仗却被强迫认为打了胜仗。
……总之是被愚弄着苟且偷生,
然后像虫子般地死去。
从那无数惨死的平民百姓中,
本片挑选了装门面的历史书上不大会言及的
东京不良场所——新宿红灯区,
和贫民区女子与孩子来进行描写。
本片关注的是被抛弃到历史背后的
花街柳巷女子和在那里生长的早熟少年
为了生存而与命运进行的顽强搏斗。
《新宿樱幻想》中扮演少年主人公的演员是通过面试招来的,然而他只在吉祥寺的井头公园参加拍摄了电影开头描写樱花如飞雪般飘落的那场戏,随后拍摄计划就取消了。可是我并没有死心,只不过对这种隐秘历史的兴趣尚未涌动起来而已。我仍然在一点点修改、润色剧本。从主人公在后方度过了早熟的思春期这一点来说,多多少少也带有我本人自传的影子。但是,主人公作为一个小学生,先是爱上了一个妓女,后来又变成同性恋者。他当时的感情状态,以我贫乏的经历来说是很难入木三分地描写出来的。这一点难度很大。
由于那位千挑万选招来的少年演员已经长大,他参加拍摄的开头那场戏也无法使用。如果想要把这部电影拍出来,还得从头重拍。
从我进入松竹开始算起,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其间,不仅小津安二郎、川岛雄三这两位师傅,就连许多同辈伙伴也已辞世。从我的早期作品开始就一直与我合作的演员殿山泰司早在1989年就已逝世,另外两个老搭档——演员西村晃和摄影师姬田真佐久也在1997年过世了;到了1999年,又一个人——今村班子中的著名摄影师栃泽正夫也撒手人寰,这对我的打击很大。
在现在的电影摄制现场,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年轻化了,他们都是些热爱电影的人。看着他们在现场生龙活虎的表现,我不禁感到日本电影还是有希望的。
1986年,横滨广播电影专业学院改制为一所专业学校——“日本电影学校”。尽管少子化浪潮导致升学人数锐减,可是来报考的学生仍然多于招生人数。以前入学只需通过面试,但报考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得教师们开始无法招架,以致有个时期不得不在面试前增设一门作文考试。
我们学校设有培养影像作家的“影像科”和培养演员的“演员科”。演员科的学生现在每年仍然要去进行创校以来的传统——农业实习。然而,最近专业农户越来越少,寻找能接受我们学生前去实习的人家也变得颇费周折,以至我半真半假地跟负责的教师商量:这样下去,看来迟早得到韩国去找农田了。我于1992年辞去校长职务改任理事长,从1994年起请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来担任了校长。
对这所电影学校的未来,我还是满怀梦想的。趁着2003年春季开始实施新的规定,我想把学校升格为专业研究生院。因为电影学校已经对来自中国、韩国的留学生打开了大门,而他们学成回国之后,要是没有研究生学历是难以施展手脚的。我还必须四处奔走,确保土地的使用,充实各种设备,为的是达到新规定中的研究生院设置基准。
人本来不会将自己的创造行为传授给别人,因为所谓创造归根结底是一种个人行为,哪怕是些许的外来帮助都理当拒绝。我一直以来也是按照这种理念来拍电影的。但另一方面,创造的态度和志向是可以传授给别人的,这种传授正是我们对年轻人应尽的责任。
不需要什么天才,
不要被常识束缚。
拿出勇气来,
执着地探求人性,
朝着无人的旷野疾奔!
这,就是我给年轻人的赠言。
前言:不上算的工作
早熟的大城市少爷
鬼今平
拍平民,拍神灵
走向创造的旷野
全作品列表
老爷子的侧影——儿子眼中的今村昌平
附录:年谱
今村昌平始终在探求人性的底线,逼视真实的丑陋与野蛮,他是导演中的人类学家。 ——戛纳电影节颁奖词
今村昌平的电影表现力朴素,但他确实是一位大师,在电影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丁 斯科塞斯(美国著名导演)
他赤裸地描写人的本能与欲望,展现了战后日本人挣扎反抗的形象,是战后日本电影界的代表人物。 --佐藤忠男(日本著名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