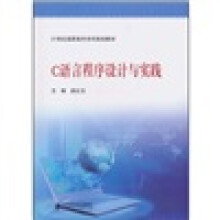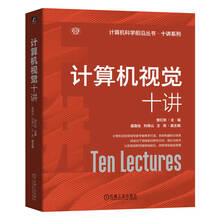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以乐观礼》:
《韶乐》是否只在齐国存在?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除周王室外,各诸侯国对于六乐只是选择性承载,这似乎有些说不通,难道诸侯国之诸子在其时没有看到和参与过这六乐就在发议论?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六乐及其礼制仪式中多种用乐诸侯国都有存在,但缺失有效记录。依照周代礼制仪式规范性用乐应该是王室与诸侯国普遍存在。考虑到音声类型的时空特性,应该考量其制度下体系内承载与使用的意义。“周官”体系规定礼制仪式王室与诸侯、卿大夫、士使用的等级差异,无论乐悬编列、乐舞佾数各不相同,乐歌、乐曲与乐舞名目存有差异。应该明确,周天子并非只在王室,当其到诸侯国巡视,依《周礼》与《仪礼》制度规定性必须使用的乐舞形态该如何呢?当然要靠诸侯国有司以为承载,还是上下相通式的用乐把握。当这些乐舞被纳入制度规定性以为功能性使用,诸侯国若无承载群体以为不时之需,这些乐歌、乐舞是否会在诸侯国传承?所谓“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就是这个道理,恰恰是礼乐制度下功能性为用的必须导致了这些乐在各地存续。
所谓乐之礼与俗完全是世人依社会需要而赋予其功能性的意义。礼乐之定位首先来自于礼俗观念之产生,也就是礼的观念约定俗成或称约定成俗者。周公以权利将这些社会上所存礼俗观念加上自己的理解使之制度化、国家化,便从礼俗转化为礼制。这礼俗/礼制仪式中要有乐与之相须为用并在国家制度的意义上规范并渐呈体系化之时,礼制仪式中用乐的观念固化导致礼乐之存在;当礼制仪式分出不同层级,导致用乐具等级化意义;当礼制仪式分化出多种类型,导致仪式用乐的丰富性;当礼制仪式中必须用乐,那些社会上存在的、未纳入礼制仪式的乐便具“俗乐”意义。乐本无所谓礼与俗,由于礼乐观念形成,也便生发与之相对应的俗乐观念。中国传统用乐观念所谓礼与俗的两条主导脉络由此而生,这是中国乐文化“逻辑起点”,礼乐与俗乐两条脉络从此并行不悖、互为张力地前行。
结合周代礼乐来源的类型性、特别是“拿来主义”使用的一类我们似可这样认知:礼乐之存在是社会人士将社会上存在的乐纳入礼制仪式之中,或为某种礼制仪式刻意创制,在礼制仪式中为用并形成固化。我们可以此理念来认知《诗经》与礼乐的关系。所谓“风土之音日‘风’,朝廷之音日‘雅’,宗庙之音日‘颂’”。如果依照《诗经》之类分这样认知的确精到,但这《诗经》从整体意义上把握会是怎样的情状呢?无论风雅颂所记录的都是歌词,这是不具备记录乐谱或称乐曲条件下的样态,后人在判研之时忽略为乐的整体意义。依照周之礼乐有“拿来主义”一类判研,后世谓周王室将其所统治区域的乐歌收集起来以知“讽”,但收集之后仅仅将歌词内容把握,还是进一步分类为用值得考量。墨子有诗为诵、弦、歌、舞的认知,实质内涵就是音声活态存在。究竟在哪些地方与场合为用呢?这既要从《诗经》文本内容加以把握,又要看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用途,如此把握这些作品在社会生活中的归属。
《诗经》“风”类作品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来自社会底层,情真意切,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形态。“雅”类作品是侧重于宫廷为用的创制,作品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颂”为“宗庙之音”,当然不会源自民间。从《周礼》与《仪礼》与《诗经》之对应性来看,《诗经》中相当部分内容与礼制仪式中的用乐关系密切,后两类自不待言,“风”类亦有选人礼制仪式为用者。
《诗经》“风”类作品选人礼制仪式为用,如《仪礼》中“乡饮酒”、“乡射礼”、“燕礼”之“乡乐”即是“周南”之《关雎》、《葛覃》、《卷耳》和“召南”之《鹊巢》、《采蘩》、《采》。以上三种礼制属嘉礼和宾礼,既然将这六首乐歌以“乡乐”归之,便为礼制仪式之有机组成,这是“拿来主义”,是《周礼》和《仪礼》中以功能性意义赋予“乡乐”者,乡乐是为礼乐的有机构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