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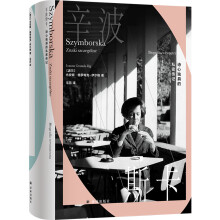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汤唯说:她短暂的一生有着无穷的魅力。
究竟,萧红的黄金时代是怎样的?
且看复旦博士邹经抽丝剥茧,为你展现萧红一生的四季轮回。
李劼、余世存、张耀杰联袂推荐
1 毒月
从日本东京回来后,萧红只身前往北京,1937年5月4日,她给在上海的萧军写信: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以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做不到……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这年,萧红二十七岁,与萧军五年的感情已濒临崩溃。距离她生命的结束,也还只有五年。
同是在北京,十年之前,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而1927年夏,萧红为继续读书,与家庭长达一年的抗争终告胜利。彼时,求得新知,是萧红“把自己建设起来”的朦胧憧憬。十年以后,二十七岁的萧红,其书信反映出的心境,竟与王国维二十七岁时的诗作若合符节:“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此时,死亡的阴影已“在梦中常常生起”。那么,心被浸以毒汁,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故事,还是得从萧红出生的那个“毒月”说起。
1911年农历五月,萧红呱呱坠地,地点在黑龙江省呼兰县龙王庙路南,张家大院内东边的一个炕头上。如今的呼兰已撤县划区,隶属于哈尔滨市。这是一个“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的地方。
呼兰过去并不怎样繁华,但张家是殷实的、富足的,也曾是有头有脸的。张家大院占地约七千平方米,分东西两院,共有房舍三十余间。张家人主要居住在东院,此院建有五间正房,其中四间住房,祖父母住两间西屋,父母住两间东屋──正是萧红出生的地方。
萧红七岁之前,都与父母住在一起。1917年夏天,祖母范氏病故,萧红执拗地要搬去与祖父住。在这屋里她可以尽情地“喊诗”,声音高亢得能将屋顶掀掉。除了祖父的房间,她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乐园”,那就是正房后面占地近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不过,秋雨过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不久,大雪便落下来,通往后园的门,以及整个后园都会被封锁住。
张家西院一般用来储存粮食等杂物,空余的房间便出租给当地的佃户和一些做小生意的穷人──卖猪的、开粉房的、赶车的、磨面的……萧红自小便与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们接触。奇怪的是,她似乎对这些“劳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萧红十六岁上初中,一次绘画课上,她所喜爱的美术老师高仰山在教室里放置了一些静物,供学生素描。萧红对那些水果、花卉、陶罐、骷髅提不起兴趣,却跑到老更夫那里借来了一杆黑色的烟袋锅子,并将其靠在一块褐色的石头上,画将起来。高仰山后来为这幅画作命名为《劳动者的恩物》,萧红感到很满意。
或许,“地利”为萧红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而“天时”却给这位天才女作家的身世预设了第一桩迷案。
──李劼(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
萧红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经验并表达了中国女性的精神高度,她的柔弱之极的强大、感知纯真的鲜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鲜有人可与之相比。邹经这部女性视角的萧红传记对传主深具同情之理解,读本书让我们重新了解萧红,重新发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余世存(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
邹经女士用女性眼光写作的《萧红传》很是平实生动,其中发掘呈现了许多我所没有看到的新材料。我认为,是萧军所谓“性的冲动”和“正义冲动”决定了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一代知识人既盲目冲动又人身依附的人生曲折;那一代人最为缺乏的是自由自治、契约平等、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的“自我规定的意志”。——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