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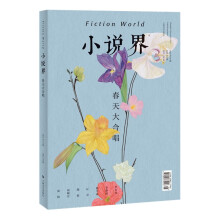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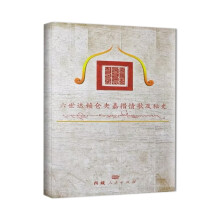



“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卡洛斯·富恩特斯首部作品;
完整中译本首次面世;
带我们窥探面具背后不愿示人的秘密。
短篇小说集《戴面具的日子》首版于1954年,是“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墨西哥文学大师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平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全书由六篇充满了文字和思想活力的短故事构成,有对于人类文明的宏观思考,有指向美苏冷战的政治讽喻,有对外族入侵和开明君主的悲剧认同,有对巴拿马运河的离奇隐喻,有对阿兹特克神祇的敬畏,还有对最终毁灭文明的消费主义的嘲讽。整部作品充满了奇思妙想,开篇的《查克•莫尔》更是富恩特斯为世人称道的短篇之一。
查克•莫尔
前段时间,菲利韦托在阿卡普尔科淹死了。就圣周的时候。他被水利部开除了,但还是没经住官僚气的诱惑,像每年一样去了那家德国小旅馆,吃热带厨房的汗水加甜的腌酸菜,圣周六到戈布拉达跳舞,在奥尔诺斯海滩暮色笼罩的陌生面孔中自我感觉是个熟脸儿。是,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很会游泳,但现在,上了四十,身体每况愈下,想游过这么长一段,还是半夜里!穆勒太太不让在旅馆里守灵,说是老主顾,只在拥挤闷热的小天台上搞了个舞会;就这样,一脸惨白躺盒子里的菲利韦托为了等早班车,在各种背篓包裹陪伴下度过了新“生”活的第一夜。我早早赶来给棺材装车的时候,菲利韦托正在一座椰子堆成的坟头底下,司机让赶紧挪到车顶上去用帆布盖起来,免得把其他乘客吓着,还担心我们给他招来晦气。
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时候还有一丝儿小风,等到了迭拉科罗拉达,热和光都上来了。就着鸡蛋香肠早饭,我打开菲利韦托的公文包——头天跟其他东西一起从穆勒旅馆领回来的:二百比索、一份在墨城被禁的报纸、几张彩票、去程车票(只是去程?),还有那个廉价笔记本,画成小方格的内页,大理石纹封面。
在一个个大弯、呕吐的恶臭和对已故朋友私生活某种自然的尊重之中,我鼓起勇气读起他的日记来,似乎想起了——没错,从这儿开始——办公室里那些日常的工作,也似乎理解了他为什么越来越颓废、忘事,为什么发些没意义、没编号、没“有效投票”的公文,为什么那么老的资历还最终被踢走,退休工资也泡汤了。
“今天去办了养老金。办事员那人真不错。我很满意,决定去咖啡馆花上五比索,就是当年我们老聚、现在我再也不去的那家,因为它总提醒我二十岁能比四十岁允许自己更多的挥霍。那时候我们还都在一个水平上,会正义凛然地反驳任何对同学的轻视,而且跟那些说谁出身不好或者没气质的人还真干过架。我以为很多人(可能是最低微的)会爬很高,在这儿,学校里,可以结下长久的友谊陪着渡过汹涌大海,然而不,事情没有发展成那样,无所谓规则定律,不少穷酸的依然穷酸,很多比在友好热烈的聚谈上预言的更有出息,另外我们这种当时看着前程远大的半路抛锚,给个补考弄得整个人都掏空了,被一道人生赢家和一事无成者之间看不见的代沟隔绝开来。总之,今天我又坐到那些椅子上——更现代了,还有自助饮料机,像一场侵略中的街垒——准备好好看看档案。我望见好些人,变样了,健忘了,被霓虹灯照亮了,飞黄腾达了;他们跟我几乎认不出来的咖啡馆一起,跟城市本身一起,用一种跟我不同的节奏逐渐雕琢着自己。不,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或者不想认出我,最多——有那么一两个吧——用一只又肥又快的手在肩膀上拍拍。慢走啊您,招呼不周。他们和我中间横亘着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那十八个球洞。我把自己藏进档案里。充满期待、乐观预测的岁月鱼贯而过,阻碍其实现的所有缺憾也一一陈列。我突然很着急,急不能插手过去,也粘不起扔开了好久的拼图块,玩具箱总会被逐渐忘记,最后谁知道小锡兵、头盔和木剑给丢到哪里,再心爱的面具也都一样。有过确信、纪律、对责任的坚持,不够吗?还是太过了?有时候,对里尔克的回忆不断纠缠我。死亡是青春冒险的巨大报偿,年轻人,何不带上所有秘密出发?今天,我将不用再回望那些盐城。五比索?加两个当小费吧。”
“佩佩除了特别热衷研究商法,还喜欢把事情理论化。他看见我从主教座堂出来,陪我一起走到国家宫。他已经不信教了,这还不够:走半条街就得制造一个理论,比方说,他要不是墨西哥人才不会信基督呢,而且——不是,你看哈,很简单,西班牙人来了,叫你拜这么一位上帝,肋旁被刺,血肉模糊,钉在个十字架上。被牺牲的人,被敬献的人。一种跟你全部仪式、整个生活这么接近的感情,可不就自然而然接受了吗?反过来,要是墨西哥被佛教徒或者穆斯林给征服了呢?让我们的印第安人崇拜一个死于消化不良的人,想象不出来吧。但是一个不光要人给他献祭,还让人把他心挖出来的上帝,嘿,真把威奇洛波奇特里将了一军!从狂热、血腥、注重奉献和仪式的角度看,基督教是土著信仰一种新奇但又自然的延伸,悲悯、仁爱、另一半脸的方面则被屏蔽了。在墨西哥就是这样:要信什么人,先得杀了他们。
“佩佩知道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一些墨西哥原住民艺术,收集小雕塑、神像、盆盆罐罐,周末都在特拉斯卡拉和特奥蒂华坎转悠。大概就因为这样,我花钱他总结,还老跟这些话题扯在一起。对了,我好长时间一直想找尊满意的查克•莫尔复制品,今天佩佩告诉我说拉古尼亚有家卖,石质的,要价也不高。我星期天去一趟。
“有个人真讨厌,把办公室饮水桶的水染红,大家全乱套了。我去跟主任汇报,他居然乐得不行,结果那个元凶整整一天都在到处张扬、挖苦我,水来水去的,切……!”
“今天星期天,我抓空去了拉古尼亚,在佩佩指的那家小店找到了那尊查克•莫尔。确实漂亮,真人大小。店主说保证是真品,我不信。石料很普通,不过不影响造型的优美和整体的紧凑。狡猾的卖家在他肚子上抹了番茄酱,好向游客吹嘘他血腥的真实性。
“把那玩意儿搬回家可比买还贵,好在总算是送到了。暂时放地下室,收藏间得重新摆放给他腾地儿。这种神像需要太阳,直射的、火热的,这是他的元素和条件。地下室黑咕隆咚真埋没他了,模糊一团、奄奄一息的样子,好像还做出鬼脸怪我不给他光。之前卖家有一盏射灯正好垂直打下来,把所有棱线变得柔和,给我的查克·莫尔一副更和善的表情,我也得学学。”
“一早醒来发现水管坏了。糊里糊涂地,我让厨房跑着水,漫出来流了一地,直灌进地下室都没发现。查克•莫尔扛住了湿气,可旅行箱都毁了。偏还是个工作日,搞得我上班都迟到了。”
“终于有人来修水管了。箱子彻底废了,查克•莫尔底座也长了青苔。”
“半夜一点,醒了,有种痛苦的呻吟,听着毛骨悚然。是不是进贼了。瞎想。”
“夜里的哀号还在继续,不知道什么东西,总之弄得我很紧张。更烦的是水管又坏了,雨也浸进来,地下室全淹了。”
“水管工不来,我绝望了。墨城的水务局真别提了。雨水不走地漏直往地下室灌,这还是第一次。不过呻吟声倒没了:一样换一样。”
“地下室抽干了,查克•莫尔长满了苔,样子很恐怖,全身像中了绿色的丹毒,只有两只眼睛除外,保留了石头的质感。星期天我来把苔刮掉。佩佩建议我换个公寓,住顶层,免得再发这种水灾。但是我不能扔下这座宅子,一个人住是大了点,波菲里奥时期的建筑风格也有点阴森,可这是对我父母唯一的继承和回忆了。要是街边半地下室是带自动点唱机的冷饮店,一楼是家装修店,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我去用刮刀刮查克·莫尔身上的苔——像长进石头了,弄了一个多小时,下午六点才完事。光线不好,收工的时候沿着轮廓仔细摩挲,感觉每摸过一遍石料就变软一些。我不愿意相信:简直像面团一样了。拉古尼亚那人把我蒙了,什么前哥伦布时期雕像,纯粹是石膏,一受潮就完了。我给他盖上几块布,趁还没全坏,明天搬楼上去。”
“布在地上。难以置信。我又摸了摸查克•莫尔,变硬了,但还没恢复成石头。我都不想写下来:躯干有某种肌肉的质地,按一按,橡皮似的,感觉有东西在这斜卧的雕像里流动……夜里我又下去一次,没错:查克•莫尔手臂上有汗毛。”
“我从来没这样过,办公室的事儿弄得一团糟,汇了一笔还没授权的款,主任都提醒我留神了;对同事可能也不礼貌。我得去看医生,问问是我想象力太丰富还是神志不清或者别的什么,另外还得把那该死的查克•莫尔处理掉。”
到这里,菲利韦托的字还是他平常的样子,宽宽的,有点椭圆形,我经常在备忘和表格里看见;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却像是另外一个人写的,有些地方像小孩,费劲地把每个字母分开,有些又显得紧张,轻得认不清。断了三天,故事重新开始: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然后人就信以为真了……但这确实是真的,不光是我信的问题。水桶是真的,开玩笑把水染红就更真,因为这会让我们更好地注意到它的存在,或者说‘在’……真实是倏忽即逝的雪茄烟圈,是哈哈镜里的怪物形象,所有死去的、活着的、被忘记的,难道不真?如果一个人梦里穿过天堂,有人给他一朵花作为到过那里的证明,醒来的时候花就在手上……那怎么说?……真实:有一天被打碎成一千片,头落在这儿,尾巴掉在那儿,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她巨大身躯上散失的碎片之一。海洋自由虚幻,只有囚进海螺的时候才变得真实。直到三天前,我的真实还停留在今天被抹除了的那个层面:条件反射、例行公事、会议纪要、公文包。之后突然,像某天震动起来的大地(让我们想起她的伟力),或者总有一天会来的死亡(谴责我对人生的渐忘),另一种真实昭示出来,虽然从前也被感知,但一直无主似的游荡,现在重来震撼我们,试图恢复生机和话语。我再次以为是我的想象:柔软优雅的查克•莫尔一夜之间变了颜色,黄色,几乎金色,似乎指示我他是一个神,目前还隐忍不发,但膝盖已经放松了不少,笑容也更和善了。昨天,我突然惊醒,慌乱地确定夜里有两个呼吸声,黑暗里跳动着我自己之外的更多脉搏。是的,楼梯上有脚步声。噩梦。继续睡……不知道努力了多久,再睁眼的时候天还没亮。房间里一股恐怖、树脂熏香和血的气息。我摸黑把房间巡查了一遍,最后停在两个闪光的小孔上,两个冷酷发黄的三角旗形状。
“差点背过气去!我打开灯。
“查克·莫尔站在那儿,挺直了,面带微笑,赭黄色,肚子肉鼓鼓的;两只细眼睛都把我看木了,斜吊着,跟三角形的鼻子贴得特别近;下排牙齿紧咬着上嘴唇,不动,只有大得过分的头上那个方形冠的闪光透出一丝活气。查克·莫尔朝床走过来,雨开始下。”
我记得菲利韦托是八月底被部里解职的,主任当众批了他,还有传言说他疯了,甚至偷东西。我不信。是有一些混乱的文书,他问处长水有没有气味能闻见,向部长主动申请去沙漠降雨。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吗,是不是那个夏天雨太多让他脑子进水了,或者住那座老宅子造成了什么精神上的抑郁,毕竟一半房间都锁着落灰,没有仆人也没有家庭生活。接下来的日记就到了九月底:
“愿意的时候,查克·莫尔还是可以相处的……让人陶醉的汩汩水流声……他知道很多神奇的故事,季风啦、赤道雨啦、作为惩罚的沙漠啦;他神话级别的父神地位也由每种植物揭开:柳树,离经叛道的女儿;荷花,宠儿们;仙人掌是岳母。我不能忍受的是他的气味,出离人类,在这身不是肉的肉体和闪烁远古气息的拖鞋上挥之不去。带着尖利的笑声,查克·莫尔讲述他是怎么被勒普隆荣发现、跟崇拜其他偶像的人混在一块儿的。他的精魂经历过水罐和暴风雨,那很自然,但他的石身是另外一回事,把他从隐藏的地方挖出来是人为的、残酷的。我想查克·莫尔永远不会原谅这件事。他知道美学事件的急迫性。
“我按理该给他准备Sapolio皂,卖家以为他是阿兹特克人的,往他肚子上抹了那些番茄酱,得好好洗洗。问他跟雨神特拉洛克的亲缘关系好像让他不怎么高兴,生气的时候,那本来就很恶心的牙齿露出来锃亮发光。头几天他还回地下室去睡,昨天开始,睡到我床上了。”
“旱季开始了。昨天,从我现在睡的厅,又开始听见最初那种低沉的呻吟,然后是一片稀里哗啦的声音。我爬上楼,把卧室门推开一半:查克·莫尔正在砸灯和家具;他张开被划伤的双手扑过来,我赶紧关门躲进浴室……后来他喘着粗气下来要水喝,让各处水龙头整天开着,屋里找不到一厘米干的地方。我睡觉都裹得紧紧的,求他别把客厅弄得更湿了。”
“查克·莫尔今天把客厅淹了。我气坏了,说要把他送回拉古尼亚。他狞笑起来,不同于任何人或动物的尖利声,更可怕的是他给了我一巴掌,举着满臂的粗大手环甩过来。必须承认:我成了他的俘虏。我最开始可不是这么想的:我以为是自己占据了查克•莫尔,就像占有一个玩具,大概是小时候那种安全感的延续吧,但是童年——谁说的来着——是被岁月吃掉的果子,我没注意罢了……他穿上了我的衣服,长出绿苔的时候就换成罩袍。查克·莫尔习惯被顺从,时时处处,而我不是发号施令那种人,只能一再屈服。只要不下雨——他的神力呢?——他就总是狂躁易怒。”
“今天我发现查克·莫尔晚上老出去,每天天黑的时候,哼起一首走调的歌,很古老,比歌唱本身还要老,然后突然没声。我敲了几下门,没有回应就壮胆进去。那个卧室我从差点被攻击那天起就没再进过,现在几乎一片废墟。渗透整座房子的那股血和熏香的气味在这里尤其浓烈。门后一堆骨头,狗的、猫的、老鼠的,这是查克·莫尔晚上出去偷的给养。难怪每天清早那让人心惊肉跳的叫唤。”
“二月,天气干燥。查克·莫尔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还让我给一家餐馆打电话,叫人每天送鸡肉饭来。但是我从办公室弄的钱已经不剩多少,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一日开始,因为欠费,断水断电。结果查克又发现了离家两个路口的一座公共喷泉,逼我每天给他提十到十二趟水,他在阳台上监视着,说要是想逃的话就当场劈死我。他也是闪电神。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夜行活动……因为没电,我八点就睡觉。按理说应该习惯查克·莫尔的存在了,可不久之前,在一片漆黑的楼梯跟他撞上,我还是差点没吓得喊出来,他手臂冰凉,焕新的皮肤上长着鳞片。
“如果再不快下雨,查克·莫尔会重新变成石头。我发现他近来行动开始吃力,经常一连几个小时斜躺着,一动不动,好像又是尊雕像了。不过这些休息又给他新的力气折磨我,抓我,好像能从我肉里挤出什么汁儿来。从前给我讲老故事的友善间隙已经没有了,我只注意到加剧的怨恨。还有一些别的迹象让我更不放心:酒窖快空了,他把我晨衣的绸子摸来摸去,想叫我雇一个女仆,还让我教他用香皂和乳液。我觉得查克·莫尔正在一步步陷入人世的诱惑,曾经看上去永恒的脸几乎出现某种老态。这或许是个得救的办法:如果查克·莫尔变成人,说不定活过的几百年积压成一个瞬间,他也会被雷电劈死。不过这或许同时酝酿着我的死亡:查克绝对不会想让我看见他的崩溃,他可能要杀了我。
“我今晚要趁查克夜游的时候逃掉。去阿卡普尔科,看怎么找个工作吧,等查克•莫尔死掉。快了,他头发灰白,身子都浮肿了。我得去晒晒太阳游游泳,恢复一下体力。还有四百比索。住穆勒旅馆,便宜还舒服。就让查克·莫尔占着这儿:我倒想知道没有一千桶水他能撑多久。”
菲利韦托的日记到这儿就完了。我不愿再想他的故事,直睡到库埃纳瓦卡,从那儿到墨西哥城的路上,才试着把记录理出些头绪,跟工作太忙联系起来,或者加点心理问题;晚上九点到站的时候,还是想象不出他到底发了什么疯。我雇了辆车把棺材运到菲利韦托家,准备在那儿安排葬礼。
没等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面前一个黄皮肤的印第安人,穿着家居服,戴着围巾。他的样子恶心得不能再恶心了,廉价花露水味儿,扑了厚厚一层粉想掩盖皱纹,嘴上拙劣地抹了些口红,头发像是染过。
“抱歉……您可能不知道菲利韦托已经……”
“没关系,我什么都知道,请让他们把尸体抬到地下室去。”
查克•莫尔
为麦利一辩
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
兰花连祷
因神之口
发明火药的人
译后记
阿兹特克人是墨西哥人数最多的一支印第安人,曾于西班牙人入侵美洲前建立帝国,对墨西哥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形成曾产生深远影响。阿兹特克人使用的历法有神圣历和太阳历两种,其中的太阳历又称哈布历。根据该历法,一个月由20天构成,一年有18个月,再加上5天,作为最后的一个小月,全年一共是365天。而最后这5天,便被称作“戴面具的日子”,或“戴龙舌兰叶子”的日子。
受过良好的西欧教育的卡洛斯•富恩特斯,是一个标准的“土生白人”,在别处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祖国是如此面目模糊,仿佛戴上了面具,隐藏了自己不愿示人的样子,或者秘密。想要了解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文学世界,《戴面具的日子》是不容略过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