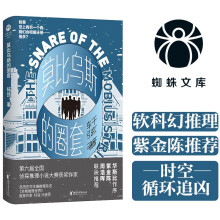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国家航海(第十一辑)》:
官渡及私渡的管理,统归于地方州县。然而其管理并非一般意义的针对渡口的单一的管理,而是一套融合了涉及船户及船只法令的交叉管理体系。依照规定,私渡船户需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饷银,才能在渡口进行有偿的营运。如澄海的私渡船户,必先至官府处获取“牌票”,有了“牌票”便具备官府承认的营运资格。
牌票事实上可以理解为州县给予船户及其船只的备案凭证,船户在申请牌票的过程中,同时也被纳入到官府的监管之下,船户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责,其私人船只也必须按照规定进行登记。
渡口船户受到严格的监管,官渡及私渡船户,都须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或由地方绅士担保,其邻接户族亦互为担保。《大清律例>有针对渡夫的行为规定:
“若撑驾渡船梢水,如遇风浪险恶不许摆渡,违者笞四十;若不顾风浪,故行开船,至中流停船勒要船钱者,杖八十;因而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或不曾勒要船钱,止是不顾风浪,因而沉溺杀伤人者,以过失科断。”
另外,依照条文,渡口船只的大小、航程、载人额数、渡夫的姓名、往来的渡口等信息必须登记在案。“每船置大白粉牌一面,将渡夫姓名、往来埠埗、船身梁头丈尺、水程里数、载人、收钱各数目,及归何处捕巡、河泊所等官管理,逐一开载。”
通过这些规定,船户之间、船户与担保人之间形成了责任承担甚至是连坐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监视、影响。这些针对船只及船户的法令强化了渡口的有序管理。
另一方面,随着清代韩江流域义渡、私渡等民间渡口的大量涌现,官府与这些渡口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渡口管理的成效。在上述法律条文以外,渡口的管理实际上还须落实到渡口占有者身上。另外,私渡之间的恶性竞争,通常需要地方官员出面协调。
虽然官方史书对海阳县官渡、私渡的记载较少,使我们无法具体掌握官渡的经营管理情况。不过,近年来在韩江沿岸所发现的几通石碑恰恰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清代韩江渡口的运营及管理情况。
道光二十五年,海阳县的两个私渡渡口船户张大胡与许阿乙之间因越界搭载乘客而产生纠纷。据载,事件的起因是,船户许阿乙强行进入张大胡的地界内搭载乘客并且霸占了张大胡的渡口。张大胡在试图与对方交涉的过程中遭到对方邀集的族众的围殴,势单力薄的他只好向官府求助。当时的海阳县县令吴均判决:许阿乙因恃强凌弱,被勒令归还强占的地界。为杜绝后患,知县吴均在双方地界的交接处立了石碑,明晰了双方各自渡口的运营范围,同时也警告其他的企图越界侵占的行为。
另一起纠纷发生于同治十二年,此时渡头的经营权已发生转变。张祥汉与王得合各自越界搭载,互相控诉。海阳知县夏献铭亲自做出裁决,断定天后宫至乌奶藤,北堤雨亭至白沙宫为张祥汉地界,王得合则拥有上水门接官亭至西门脚茶亭,新堤至天后宫地界的营运权,双方均不得再越界,官府的态度表明了对于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惩戒的决心。这种越界侵占的行为无非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韩江商业的繁荣直接刺激了此类的利益争斗。
光绪二十一年的一通碑记记载了蔡姓与黄姓两个宗族为争夺同一个渡口而产生的纠葛。事件中的蔡姓宗族占有水头渡口的营运权,同时另外一个位于上铺乡的上铺渡头亦归蔡姓所有。此后,上铺乡一黄姓宗族亦在上埔乡设渡口,遭致蔡姓的阻碍,纠纷由此产生。从黄姓与蔡姓的纠纷中,我们看到当时惠潮嘉道台联元的态度,“尔今者设渡船要霸住全河,虽由上埔乡来往,却不准上埔乡设渡.尔等系奉何处明文!即使黄以雅等勉强退让,上埔乡愚民甚多,能全退让乎?以天下无是理也。假如曾前道徇黄姓之私,断令渡船此时应全归黄姓,尔等蔡姓获利已久,早应更换。或断令黄姓渡船亦准至马头宫,与尔蔡姓无异。……今黄姓亦准设渡船,稍分客人过上埔者之利,客人经过上埔,该乡借获蝇头微利,谁日不宜?尔等后思从前仅有水头渡船,今又添上埔渡船,似乎有所更改,殊不知河仍可因积沙而更改,区区渡船何不稍为增益”。联元站在弱者黄姓一边,认可了黄姓在上埔乡设渡口,制止蔡姓试图独占渡口的行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