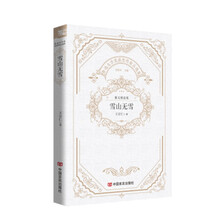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精彩试读]
春天最初是闻到的
文_冯骥才
一年一度的此时此刻,我都会站在料峭的寒气里,期待着春天的到来。因为我知道,若要“知春”可不能等到“隔岸观柳”,不能等到远处河边的柳林已经泛出绿意,或是那变得松软和湿漉漉的土地已经钻出草芽-那可就晚了。春天的到来远比这些景象的出现早得多,一直早到冬天犹存的天地里。你把冻得发红的鼻子伸进挺凉甚至挺冷的空气中,忽然,一股子清新的、熟悉的、久违的气息,钻进鼻孔,并一下子钻进你的心里。它让你忽然感到天地要为之一新了,你立即意识到春天来了!
可是,当你伸着鼻子着意一吸,想再闻一闻这神奇的气息时,它又骤然消失,仿佛一闪即逝。你环顾四周,仍是一派冬之凋敝、天寒地冻。然而,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气息忽又出现。就像初恋时,你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的似是而非。当你感到“非”时便陷入一片空茫,在你感到“是”时则怦然心动。原来,春天最初是在飘忽不定之中,若隐若现,似有若无。它不是一种形态,而是一种气息-一种苏醒的大地散发出的生命的气息。
这时,你去留心一下。鸟雀的叫声里是否多了一点儿兴奋与光亮?那些攀附在被太阳晒暖的墙壁上的藤条,看上去依旧干枯,用指甲抠一下它黑褐色的外皮,就会发现这茎皮下边竟是鲜嫩鲜嫩的绿。春天不声不响地埋伏在万物之中,这天地表面依旧如同冬天那样冷寂而肃穆。但春天是一种生命,凡是生命都是不可遏制的。生命的本质是生,谁能阻遏生的力量?
冬天没有一次关注过春天,也永远不会关注春天。春天在出现之前,已经急不可待地把它的气息像精灵一般散发出来,透露给你。所以,春天最先是闻到的。
故此,我喜欢在这个季节里,静下心来期待春天与寻找春天,体验与享受春天初至那一刻特有的诱惑。
这种诱惑是大自然生命的诱惑,也是一种天地更新的诱惑。去把冻红的鼻子伸进这寒冷的空气中吧。
南京的鳞爪
文_匪我思存
南京是一座温润的城市。
一直以来,从来没有觉得哪座城市比它更像一块玉,它并不是近代才昂贵不菲的翡翠,而是一块温润的羊脂白玉,不剔透,但是内敛,如君子,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那种审美,底蕴厚,所以对什么都透着一点儿不在乎,有自己的骄傲和矜持,所以偶尔也斜眼看人。六朝古都的金陵,见多了世间的物换星移、悲欢离合。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玄武湖畔的月色,鸡鸣寺外的梅花……从魏晋开始,这座城市的命运几乎就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记得有一次跟朋友聊天,说起南京,我想了想,说:"南京有世家气。"她大笑,觉得我用词很奇怪。但确实如此,新兴的城市固然有一种蓬勃的生机,而那些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有的气质苍凉,有的气质冷峻,有的气质严肃,有的气质端庄,有的似老者般稳重和敦厚,有的如倾国红颜却薄命叹惋,有的像小家碧玉一样温柔,有的则有着世家公子的从容。
说起南京,可写的地方似乎很多。明孝陵的神道上种满了银杏树,秋季的时候一片金黄,背包的外国游客一边走一边拍照。梅花山麓的居民将这里当成公园,偶尔在水畔钓鱼,偶尔去林间登山。游客多的时候,也有成群结队的旅行团,但南京人自己是不大当一回事的。曾经在明孝陵的水井旁遇见一位老太太,独自带着一大杯叶子茶来登山,问及常来常往的理由,不过是山间空气好,就好比北京的老太太常去爬香山。几百年的景点,相对几千年来的城市文化,不过是司空见惯。
南京得天独厚,有江,有湖,有山,皆离城市近,就连路旁的法国梧桐,虽然是国内最常见的行道树,却也比其他城市的更高大。无他,时间厚爱这座城市。它经历得多,经历得久,法国梧桐树引进国内,首先就是在这座城市尝试种植。玄武湖那么大一片苍茫的碧水,就那样随随便便搁在火车站前。对于有几千年历史的湖泊而言,火车站算是新鲜的小不点。
每次出入南京火车站,都会觉得气韵开阔,城市的大气就是从这种不经意的地方透露出来。后来建了南京南站,现代化的建筑如机场一般,高架桥四通八达,但想到那碧波荡漾的玄武湖,还是觉得南京火车站更令人怀想。
南京的吃食,亦是叫人想念。奇怪的是,我所怀念的南京的风物,都是并不昂贵的。比如糖芋苗,比如桂花糖藕,还有一种并不精致的点心,叫梅花糕。街头巷尾,热气蒸腾地烤出来,上面撒着红绿丝,还有小小的糯米粒。我最喜欢的馅是豆沙馅,咬一口滚烫。梅花糕近年来有所改良,除了豆沙,还有水果馅甚至冰激凌馅的,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既有传统,亦不乏新鲜。
上次去南京,依旧去吃"南京大排档"。这家店以南京小吃为主,是连锁店,常去的那家就在德基广场的七楼。同一层的全是所谓的精致时尚餐厅,就他家生意最好,门口等座的队伍最长。叫号的师傅上了年纪,甚是风趣好玩。我在门口的长凳上等了一会儿,恰巧抱着琵琶的母女俩上台,唱了一段温柔动人却听不懂的苏白。台下人声嘈杂,还有小孩子的嬉闹,年轻的评弹师傅笑意盈盈,一点也没有其他同类表演的生硬和倨傲。
其实南京人是不讲苏白的,而是讲南京话。历史上有几百年时间,南京话都是所谓的"官话",全国通行。所以有时候会有奇怪的念头,把那些笔记体的小说或散文用南京话来念,又是何种韵味呢?不过张爱玲倒是在《半生缘》里头写过一笔南京话:叔惠和翠芝在玄武湖划船,写到叔惠听见南京话叫"大姑娘"音为"夺姑娘",所以她也学着船家叫"夺姑娘"。南京话不像
苏白那样温软,略沾染了北方方言的脆劲。
去过数次南京,很奇怪一次也没有去过夫子庙。有一次我甚至去看了南京大学的校园,却没有想起去秦淮河边走走。凡是游客多的地方,我总有一种逆反心理。就像中山陵,一次也没有去过。2012年6月的时候,陪父母到南京,终于去拜谒中山陵。数百级台阶,爬上去并不觉得累,最后站在陵堂之前俯瞰,长风浩浩,衣袖皆凉,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后来搭电瓶车下山,正巧坐最后一排,于是一路倒着下山,却比坐在第一排更为有趣,因为视野无遮无蔽,满目苍翠欲滴,皆是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山风微冷,甚至有些寒意。
去南京的次数虽多,每次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第一次去总统府,正是早春,总统府中数株比屋檐还高的木兰,开着冰清玉洁般的花盏,让人觉得春深似海。这次去,又见着一大树枇杷,黄澄澄压得树枝都弯了。而有一次冬天去,恰巧走到原来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满院寂无人声,松柏苍苍,仿佛云在青天水在瓶。而慢慢走出来,来到前头的院子里,却又有一大树齐檐高的茶花,开得如火如荼。
总统府和其他景点有年票,所以南京人日常持票皆可出入。这个景点的旅行团最多,却也只是集中在正中间的八字廊附近。而四季不同,见到的动人之处亦有不同。这次去,两江总督府旁的跨院里,靠墙搁着两口大缸,里面种的碗莲已经开出粉艳的花朵,外面人潮汹涌,这里却静得出奇。再往里走,又有桂树和瘦竹,绕出曲曲折折的小庭院,有山石池塘,像是小公园的模样。江南隽秀,常常在这种不经意的回眸之间。
南京人对这些地方,有一种司空见惯的从容。夫子庙,南京人也是不赞成我去的,倒是建议我去湖南路,说那里的吃食才地道。遇上出租车司机,干脆建议我就到总统府旁的"南京1912",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喜欢那种地方。"
自从上海有了"新天地"之后,国内的城市总有那么一两个类似的去处,比如"武汉天地",又比如"南京1912",都是老房子改成的餐厅和酒吧,优点是离市中心近,小资氛围十足。我老老实实对司机说:"我还是愿意去吃小龙虾。"江和湖的城市,许多地方都有点类似,就好比小龙虾,武汉有,南京亦有。记得去年走高速公路,一路上皆是盱眙小龙虾的广告。小龙虾这种东西好就好在在夜市的摊位上,也能炒得新鲜热辣。
南京菜还有一道“藜蒿香干”,这是湖泊多的城市人人都爱的时鲜菜。藜蒿原来是长在湖边的野菜,所以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苏人都爱吃。南京人春夏之交的时候讲究吃籽虾,小小的淡水河虾长满了籽,虾肉晶莹,入口鲜甜,比小龙虾金贵很多,价钱也昂贵许多。而且季节一过就没有了,是真正的时鲜货。
每个身在美丽城市的人,其实也会惦记另一座美丽的城市,这就是家乡与异乡的区别。我们在家乡生活,坦然从容,这座城市对我们而言,有着人间烟火气,是平常过日子的温馨。我们去异乡旅行,看到不同的风景,那座城市对我们而言,是花与果的淡淡香气,有未曾见过的景色,未曾尝过的食物,未曾见过的人。
这或许就是旅行的意义。
就像南京,每一次去,都发现它新的景致和不同,隔着六朝金陵的烟水气,每一次都是崭新的。
享受一秋一冬的生命
文_毛丹青
两年前,我开始在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开设课程。第一次上课,来了三百多名学生,课开讲了一会儿,我发现前排边上有一个座位是空的。
其他座位都满了,一个空位就变得挺扎眼,正当我纳闷之际,一位中年妇女从教室后面推着一辆轮椅走过来,轮椅上坐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他向我鞠躬表示歉意。
这个意外出场让我停顿了一会儿,不过很快我就示意他们坐到那个空位子上。那位中年妇女坐下之前,向讲台鞠了一躬,然后把轮椅拉到身前,替年轻人拿下椅背上挂着的书包。她的动作麻利,一切都很平常,并没有给大家带来特殊的感觉。
其他学生有的看着我身后的黑板,有的写笔记,对轮椅的到来并不意外,至少不像我那样出现停顿。
后来我才听说,中年妇女是这个年轻人的母亲,而年轻人身患绝症,四肢麻痹,需要用嘴巴咬住一根筷子才能敲打键盘。那位母亲总是推着年轻人到大学听课,许多学生都知道这位轮椅生的事情。每次听我的课,那位母亲总是坐在他后面,眼睛并不总看讲台,而是常常看着儿子,目光充满了慈爱。
按照校方的规定,我的课属于秋季课程,从秋季的红叶讲到冬季的飞雪。京都的秋天比冬天有情趣,所以,我的课程也感觉秋天讲得比冬天好—秋天讲故事,冬天讲理论,理论是晦涩的。
有一回,我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题目《我与宗教》,让大家写一篇报告,写一段能够联想到宗教的生活体验,哪怕是一个瞬间也好,篇幅、字数都不限。
下课后,轮椅生的母亲走到我面前,说:“先生,他只能回家写,而且写得很慢,给您发电子邮件行吗?”
“当然可以。”我一边说一边把邮箱地址写在当天发给他的资料上。年轻人始终对我微笑,坐在轮椅里轻轻地鞠躬。原来,他好像连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几天,大约是深夜,我接到他发来的邮件。以下是他写的内容,摘译如下——毛先生:其实,我是可以在课堂上写这份报告的,可是一想到自己用嘴巴咬住筷子敲打键盘的样子,总觉得不让大家看到才对,那个样子不好看。有时我还会流口水,我觉得害羞。不过,敲打键盘是我最高兴的时刻,这不仅是我与外界交流的手段,也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如果能在课堂上记录先生说的话,我会觉得更好。
请您原谅我没有做记录……坦白地说,我不懂宗教,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长,但同时我也知道我很快乐,因为现在能给您写这篇报告就是我的快乐。当这个快乐大于我对生命的担忧时,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宗教应该也是让人幸福的吧。
在后来的课堂上,每次我都可以看到这个轮椅生。他的目光是最亮的,背是最直的,听课时,他从来都不靠在椅背上。
到了今年的秋季课程,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一天,我听说这个年轻人已于去年的初冬去世,而且还听说,那些天在校园里,有时还会看到一位慈祥的母亲推着一把空轮椅走过,就像当年推着年轻人上课一样。
秋天已经过去,严冬到来了。如果有一天能在校园里与这位母亲重逢,我很想对她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默默地决定,明年秋天,我的课会把理论放在秋天,而把好故事放在冬天,驱走严寒。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