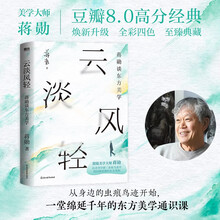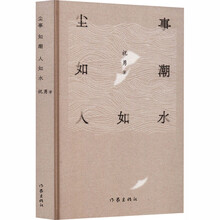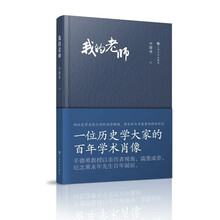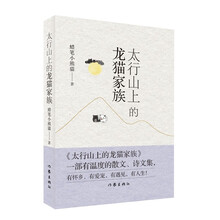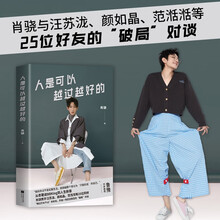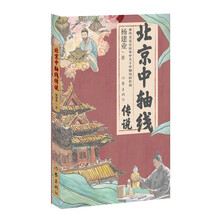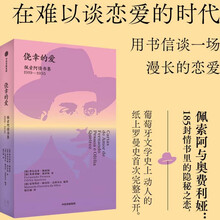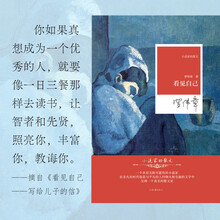我回忆起30多年前这一逸事,两人又起了恶作剧的兴致。我给远在芝加哥的梁老师打电话,以气急败坏的语气说:“坏了坏了,老丙‘屈蛇’来美国,在旧金山附近海面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截获,给关进监狱,托人捎话,要筹10万元保释金。”梁老师给吓得不轻,一个劲地唠叨:“怎么办?10万,哪里去找?哎呀,老丙,你不能等等吗?女儿不是替你办移民申请了吗?”老丙的耳朵贴着话筒,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好家伙,捉弄老师!”梁老师轻骂过一对得意门生,放心地和我们一起笑。
离开“文革”的狼烟未散的校园,是1968年,此后,我和老丙一直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友情。不冷,是因为舍不得,造反时同一个战斗队,最壮烈的一次,是某天风闻“老倮”一即将偷袭校园,子夜时分两人背着塞满石块的书包,埋伏在校门外的柑林里。好在情报是假的,若是真的,我们肯定完蛋在工人赤卫队从县武装部借来的重机枪下。往后,他上大学,我出国。他毕业后,在家乡一所中学教书,后来,转到市政府里当科级小官。不热,是因为志趣大相径庭。我爱文学,写了多年诗,好歹惹上点浪漫病,可是,老丙是不关注形而上,极端务实的人物。流行小说,他一辈子怕没读过几本,为了等车候机太无聊的缘故;至于诗,肯定是马尾拴豆腐——提也不要提。我至今记得他在结婚的前夜,邀请我去他家,两人提前睡了崭新的婚床。两个绝对不上断背山的年轻男人,聊了大半夜,先是以童贞之身,万分好奇地探讨十分“懵查查”的性事,不得要领,便转向另一话题——新娘子的妆奁。他兴致勃勃地说起家乡一带的习俗:女子过门,重场戏不在婚礼,而在出嫁路上,抬嫁妆的队伍长不长,抬笼笼箱箱用上多少名壮实汉子。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新娘子,因田间操劳而骨节粗大的手指上,“不经意地”露出来的黄澄澄的玩意有几枚。这些,当然由好面子的岳母大人操办,但新郎官自有主张。老丙奔走多天,写了好几封信,跑了好几趟县城,终于有了成果——新娘子窄腰对襟凤仙装,那领口以下刺绣的黄牡丹上,骄傲地陈列的项链,“足金,一两三钱重。她三个姨妈在香港,每人送一只戒指。我问岳母戒指一共收多少只,她说十多只,我说戒指哪有项链抢眼?找上回老家过年的香港打金师傅,熔了五只戒指加上我妈存下来的旧金牙,凑够一条项链。”我听了一半,迷糊起来,他起劲摇我,非要我发出“真的?喔,体面极了”的惊叹,才放我去找周公。不过,老丙虽然在乎尘俗功利,但作为朋友,从来是靠得住的。我每次回乡,见到老丙,都一起饮茶,吃饭,游山玩水,侃大山。他有自知之明,如果我和文明诗友聚会,他一律找个借口溜掉。
上世纪末,老丙刚过五十,提早办理退休,到了旧金山。可惜他的“洋荤”并不理想,在唐人街茶楼当了几个月收盘碗工后,回一趟老家,饭碗被年轻人抢去,争不回来。在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当搬运工,搬重物闪了腰.从此赋闲。到今年,才找到加油站收款员的半工,上通宵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