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绿意初萌
第一章 纽约,再见
我要……离开21世纪的世界
在这个城市里,你不会凝视星辰,做白日梦。你不会在早晨外出散步后,埋头翻阅平原野花手册,寻找一种途中看到的、绽放璀璨蓝色花瓣的喇叭花花名。你不会在雪地上搜寻动物的足迹,或是在这片冰封的森林里停下脚步,闭上眼,聆听五子雀觅食的啁啾。在这种时刻,你可能会忘记有蛇这种生物的存在。这种感觉就像纽约被包在一个巨大的塑料泡泡里,人类身上带着信用卡和《查氏餐馆指南》 ,端坐在食物链的顶端。本地的野生动物?不过是蟑螂、鸽子、老鼠而已,都是传染疾病的媒介,都应该被扑杀。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泡泡里展开的。
当时是2000年,一个新的千禧年露出曙光。社会各界几乎已将人们对Y2K 的恐惧抛在脑后。经济前景看好,失业率降到历来最低点,美国政府对破纪录的财政盈余多有夸耀,纳斯达克指数超过五千点,使得社会发出一阵振奋活泼的欢呼。股市让每个人都变得富有——至少在账面上是如此。在历史上最富裕的时刻,生活在这个全球最富裕国家中最富裕的城市里,希瑟和我应该觉得很快乐。其实不然。
因为这个缘故,有一天我发现我坐在出租车里,沿着公园大道前行,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因为心中藏着一个好消息而显得太过兴奋。我从车窗外看到有几头奶牛站在安全岛上的郁金香花丛里,在它们的后方,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巍巍矗立。那些是玻璃纤维做的牛。有一头奶牛身上画着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旗花纹;另一头牛的身上画着蒙德里安 式的几何线条。出租车司机朝着后视镜歪了歪头,跟我对看了一眼,然后用发音清晰、音调毫无高低变化的孟买口音说:“我总是想不通,这些奶牛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艺术。”我朝着隔开前后座的塑料防护板大声嚷嚷。
“在我的国家,牛是给人吃的。”司机说。我突然想到,印度把牛看成神圣的象征,所以他一定是巴基斯坦人。
我发现讲话不必用喊的,便说:“有时候我在想,城市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吃的汉堡是用什么做成的。星期天我推着婴儿车,带着我那一岁大的儿子去布鲁克林动物园,那里有一个女孩——她看起来绝对有十二岁了——瞪着农场动物区里的一头奶牛,竟然说不出那是什么动物。”
“一头活的牛?”
“对,一头活的牛。它只是一头小牛,但它显然是一头牛。总之,这个女孩的妈妈觉得很挫败。她一直说:‘别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这时,我儿子尖叫着说:‘哞,哞。’我简直没法相信有这样的事。”我的背靠着座位往下滑,心里想着,我的孩子不会这样,绝对不会,我感觉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不会的。然后我再次俯身向前:“我没有留在那里,看看她能不能认出山羊来。”
“在我的国家,”他说,“羊肉是最受欢迎的。”
就在这时,有一辆出租车突然插进我们的车道。“喂!”载我的司机大声喊叫,他猛然踩住刹车板,用手腕重重按着喇叭。车身的倾斜和颠簸让我的身体神经质地颤抖起来。
到了路口,我们放慢速度,穿过四面八方快速行进的路人,他们像想要盗垒的棒球选手般,快速地冲过马路。在人行道上,人们看着自己的脚,匆忙前行,嘴里喃喃自语,手上比着各种手势。老烟枪们聚集在另一栋商业大楼的柱子四周抽烟,他们的模样令人同情,烟瘾让他们魅力全失。
他们看起来都是一副走到尽头的样子,不管是抽烟的还是不抽烟的,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是衣冠楚楚的还是肮脏衰败的。每个人都显得很急切,很狂乱,仿佛快要走进坟墓。穿梭于这片水泥、玻璃与钢铁构成的风景之中,穿梭于拥挤的人群之中,他们的心思放在别的事情上,无法察觉自己的状态。直到最近,我一直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如今我离开了,走出了这个人群。
“我的孩子将会知道,牛是什么样的生物。”我做出这项宣告,我觉得我不能不跟他分享心中的好消息:“我太太和我就要搬到一座农庄去住了。”
“你是个农夫?”他一面说,一面怀疑地看着镜子里的我。
“不是。但是我要学着去做一个农夫。我敢打赌,在你的国家里,许多人还是以务农为生。我指的是一般人。为了养家活口。”然后,我的精神更加振奋,我想到这个人,还有他离开祖国到这里定居的决定:“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就是厌恶这里的情况,觉得再也受不了了?厌恶塞车,厌恶生活在锁紧的大门后面,厌恶那些可恨的事情?老天爷,你是开出租车的。你的每一天一定充满了一件又一件可恨的事情。”
司机猛然转到人行道旁,停下车子。他从镜子里看着我。我正要对他的开车方式提出抗议时,我看到了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发现我们已经到了。我付了车钱,一把接过收据,在红灯亮起、车流涌过来之前,匆忙地冲过街。
我与下班人潮走着相反的方向,走进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大厅,一个人搭电梯到17楼。在17楼,我走进《国家地理?探险》(National Geographic Adventure)杂志的办公室。这是一本新创刊的入门性质杂志,是那本深受敬重、封面有着金黄色边框的旗舰杂志《国家地理》的姐妹刊。探险——这种消遣,这种态度——现在很热门。欧内斯特?萨克里顿 置身冰天雪地的豪壮英雄史诗,还有攀登圣母峰时发生的悲剧,在书店的陈列架上随处可见。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不再是一个地区,而是一种赶上流行的宣告。在这本杂志推出前的秘密运作时期,我曾跟一位编辑见面,当时这本杂志的名字仍在严格保密中。“我敢打赌你能猜出它的名字。”他狡猾地咧开嘴笑,“它用了一个字,一个你最近随处都能见到的字。”
我对探险感到着迷。
我从小就爱看探险故事,《鲁滨孙漂流记》《一千零一夜》《山中岁月》——这本书叙述一个住在纽约曼哈顿的男孩离开城市,来到位于纽约市西北方的卡兹奇山脉(Catskills)地区,住在树洞里的日子。我曾在野地寻找印第安人的箭头,跟着我父亲在河中用盘子淘洗矿砂,想要找到金子。我曾站在父亲身旁,看着他用38口径的手枪连续开火,打死铜斑蛇。对于一个害羞的男孩来说,尽管他置身于一个死气沉沉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小镇,但是想要逃离这个社会的种种限制,来到荒凉狂野的大自然当中,这样的念头仍然在他心中激发了无限的想象。大学毕业后,我搭机前往肯尼亚,身上带着一个活页夹,里面装满地形图——用红笔圈出荒野地区的学校,还记载了如何前往两位美国教师的住所。我在那里找到一份教书的差事,在那一年中,我用桶子收集雨水,用煤油炉煮东西吃,在烛光下写短信,用无线电传送信息回家。回到美国以后,我搬到曼哈顿,担任一份推出不久的文摘《南方农夫年鉴》(The Southern Farmer’s Almanac)的编辑。(我是南方人,然而我对编辑工作和农务一窍不通。)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但我还是努力写文章,想办法登出来。最后,过了十年以后,《国家地理?探险》派我去乌干达和厄瓜多尔等地。
此刻我坐在该杂志的会议室里,心中怀着另一种探险的想法,我努力寻找合适的字眼,向坐在对面的这位年轻编辑说明我的计划。
“詹姆斯,”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国家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夜里看不到银河。”
“不知道……”
“你不觉得这件事让人感到很丧气吗?”
“是,我想是吧。”他一面说,一面皱起眉头,“但是我们今天见面,究竟要谈什么?你让我好奇得要命。”
我停下来,看着许多张用图钉钉在墙上的杂志封面。俊男美女搭配色彩缤纷的户外装备,在冰河、瀑布与半月形的海湾前,摆出各种姿势。“我再也不能写《国家地理探险指南》(NGA Guide)了。”
詹姆斯点点头,身体向后靠到椅背上。“我知道写这个要做很多痛苦得要死的研究调查工作。”
“不是因为这个。”我比自己预期的还要紧张,我顿了顿,“我要……把我自己带走,离开21世纪的世界。”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我已经被榨干了。希瑟和我正在慢慢地杀死自己,以便跟上世界的脚步。我们想试着去过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你知道的,在我们还算年轻的时候。”我向他解释我们的计划——我们想要用曾祖父时代的方式,去过自耕自食的农民生活。我们有很多细节要解决,这是当然的,但是这个计划的基本前提是:1900年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就不用。
“这意味着,”我说,“我们不会有电子邮件、电话、计算机、信用卡、水电账单和汽车保险。”
“太了不起了!”詹姆斯说,“听起来像一场货真价实的探险。”
希瑟的主管梅若是个在纽约皇后区长大的公益律师。一星期后,希瑟告诉她这件事并提出辞职时,梅若的反应却跟詹姆斯不一样。“你,”梅若说,“你疯了。”
也许我们确实是疯了。就像我们认识的任何一个纽约人一样,我们工作得太拼命了。每天晚上,我们带着工作压力回家。周末的时候,工作压力依旧尾随不去。希瑟在这家司法改革智库的工作,还有我自由接案、忙着替杂志写稿的工作,让我们不是被绑在计算机前面,就是必须到外地出差。过去两年当中,除了澳洲和南极洲,希瑟每一洲都去过了,她飞到这些地方,与当地警员进行访谈,跟政府官员举行会议。即使在怀有七个月身孕的情况下,她仍到爱尔兰发表演讲,之后飞回纽约,并在抵达纽约的当天飞往阿根廷。我们住在北半球,而她匆匆赶往的国家位于地球的另一半。我们心想,万一她生下早产儿,我们得用丢铜板来决定,孩子是在夏天还是冬天出生。
最后,鲁德算是准时在曼哈顿一家可以鸟瞰东河的医院出生。孩子才四个月大,就交给保姆照顾。我们对于必须雇用她来看孩子,对于我们只能支付她微薄的薪水,感到双重的罪恶感。(当另一位妈妈告诉我们,这位保姆把婴儿车的安全带绑上,不让鲁德下来,好让她在公园里跟人畅快聊天时,我们心中的罪恶感就更强烈了。后来我们叫她离开,把鲁德送到托儿所。)
我们花了太多钱在房子上,到户外走动的时间太少。我们从抽屉里拿出外国菜餐厅的菜单,周而复始地打电话叫外送餐点来吃。我们在转角的一家录像带店,跟隔在防弹玻璃后面的老板租来一些令人失望的电影。我们的生活里失落了某种东西——我们的感情也一样。然而我们太忙了,没法面对这个问题。至少我们是用它来当作借口。于是我们整日辛勤工作,很少谈话,到了晚上,我们精疲力竭地爬到床上,楼上公寓里两情缱绻、弹簧床“嘎吱”作响,让我们无法入眠。然而我们累极了,实在没力气让自己的床铺也这么响一下。
这不是身体的疲惫。许多世代的先人努力追求美国梦,令今日的我们受益匪浅。我们放弃了南方小镇家乡的农场和工厂的活计,用来换取接受教育和都市生活的机会。让我们受苦的不再是开拖拉机的时候出了意外,或是被在生产线不停转动的残酷机器辗断了一只臂膀或一条腿,在我们这个时代,折磨人们的是跟压力有关的疾病:焦虑症、忧郁症、电子邮件上瘾症,与有所亏欠的罪恶感。我的焦虑感在计算机挂掉的那一天达到高峰。
我的米色戴尔台式计算机——我谋生的工具——嗡嗡地停止运转,屏幕一片漆黑。我内心的慌乱越来越强烈,我用力敲打键盘,把开关键按了又按,完全没有反应。我的手指沿着插座上的电线,摸索到计算机的主机上。插头没有松脱。想到这部我不甚了解的机器,它那满是金属线的肚子里装了我所需要的大量数据,不禁感到一阵晕眩:一页页的调查研究,访谈手稿,一篇三天前就该交稿、马上就可以完成的文章,写书的构想,许多认识的人的地址,朋友和编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家人的合照,工作相关的数据,税务的数据……对我来说,这部计算机就是一切。我真是笨蛋,竟然没有作备份。
刚知道计算机挂了以后,心里冒出一阵惊慌的情绪,等这阵情绪平息后,我马上想到我爷爷。他是一位乡村医生,也是个养牛的农夫。他生于1886年。今日所谓“节省时间”的科技当时尚未出现,包括让人们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完全无法离开工作的手机,以及让人们半夜还在回复电子邮件的计算机。当人们手上使用的是以铁、钢和木材用手工制造而成的器具,他们怎能掌握现代使用锂电池的数字设施虚无缥缈的本质呢?这就是我爸爸的爸爸——在我们中间,有着这一整个时代的人——成长过程中的那个世界,跟我所理解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我领悟到,没有人知道现代化生活长期的后遗症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可以适应这一切耗尽脑汁的变迁?科技的种种进展、大量兴起的城市、日常生活飞快的步调,还有我们购买的东西和吃下的食物——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逐渐由手工全面转为机器制造。也许我不应该为了内心对科技的矛盾情感(还有计算机宕机时,我所感受到的强烈恐惧)而觉得羞愧。我心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嘶喊:停下来一分钟!你盯着计算机屏幕太久啦。你前一次挖掘泥土,或是走过田野,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更不要提你是否种过东西给自己吃了。也许我们跟自然界失去了联系,使得我们心思混乱,迷失了方向。如果是这样,也许这件事就能说明,近来我为什么如此的不快乐。也许我只是不高兴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方式顺利进行。无论是什么原因,那一天我就是想要逃离这里。
然而,我还是很本分地打电话给戴尔计算机的一位技师。我有妻小,有事业要追求,我还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几星期后,在某一个时刻,我突然在一瞬间清醒了,这个时刻改变了一切。当时我正在阅读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主题是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报导英国有一家人正过着19世纪伦敦居民的生活,并描述他们如何努力对抗这种生活的种种严酷考验。我想到我的计算机危机,这个问题依旧在脑中萦回不去——我究竟能作什么样的选择?我领悟到,原来我答案就在这里!答案不是这个真实故事的本身,而是它的核心观念——采用过往的生活技能。如果我是这么渴望有所改变,何不回到过去,用这种方式作为重新开始的起点?
我觉得,1900年是个合适的年份。我想摆脱某些科技,但我不想当拓荒者,不想徒手建造一栋小木屋,或是自己挖一口井,1900年——算是还可以回想到的时期——非常合适。我做了一点调查研究,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在1900年,农村的人口数仍然超过都市人口。在1900年,务农仍然是最主要的职业,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小农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种植、蓄养他们三餐所需的食物。在1900年,汽车——也叫作“路程计”(viamote)——仍然是件新奇的玩意儿。在美国农村地区,当时还没有电视、电话,当然也没有个人计算机。人们还是用手写信。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在1900年,你能买到卫生纸。
一个星期六,在布鲁克林一家窄小的酒馆里,我们轮流抱着烦躁吵闹的儿子。我很紧张地把这个构想说给希瑟听。她听后微微一笑,这让我记起了,我是为什么爱上她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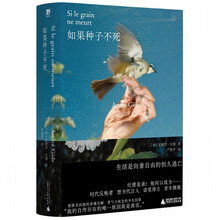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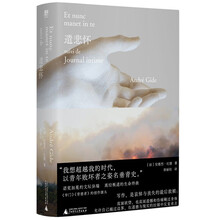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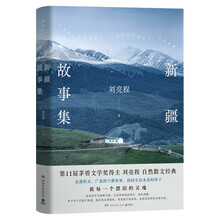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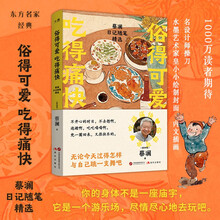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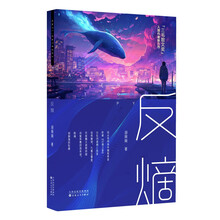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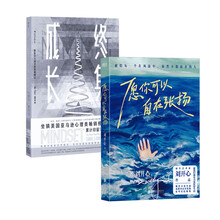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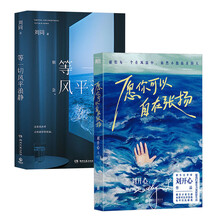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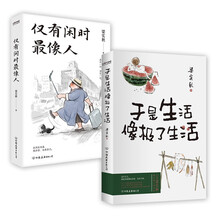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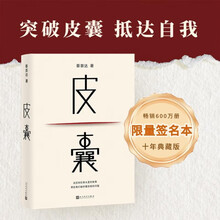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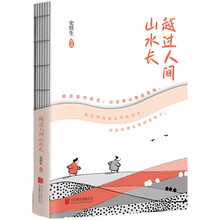
在回到古代的旅程中,我们面对了很多危险,包括用力挥动斧头,却砍到小腿;用木柴炉烤生肉,结果烟火冲天;还被一吨重的马儿踢——最让我惊恐的,就是我两岁儿子和一条蛇的对决……
——作者
这本书的价值,不是怀旧,不是乌托邦的自然之梦,而是表达了如今不少人对城市文明焦虑中的反省,用行动去反思生活,让我们看到手工农作的美好与限制。
——作家、生活家韩良露
作者回返一百年前的生活,相对的世界,究竟的心,我深心以为,他找回的是生命来自原初的那个无自性的本然真心。这点多么值得我向作者礼敬。
——作家、环境关怀者凌拂
梦想跟树很像,是浇冷水长大的!《我们没疯!一起回到1900年生活吧》这本书,不断地“浇我冷水”!它有个跟我几乎一样的梦想,却在书中写满一切“怎么这都给你碰到”的荒谬与冒险,这不断的冷水,根本就是酷夏中,迎头而来的,爽快!
——导演、作家李鼎
本书以抒情笔调描绘21世纪远离尘嚣的生活,比任何电视实境节目中的荒野求生情节还要更真实,对人更有益处。
——《出版家周刊》
从逐渐领会农场动物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到思考该如何使用难以捉摸的木柴炉;从了解自给自足的生活是有可能实践的,到成为这类社群的一份子;从努力挽回貌合神离的婚姻,到一起庆祝真正许下承诺的结合……随着这家人的生活体验,读者会感觉到自己和他们一样,不希望这段生活走向终点。本书从头到尾充满了热情、嘲弄的幽默与客观的描述,如果有任何一家图书馆,不管是公立或私立的,竟然不想购买本书作为馆藏,将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
——《图书馆月刊》
作者记下他和家人认真展开1900年生活的经过。本书笔调优美,情结感人。书中章节环环相扣,毫不造作地展现出作者一家三口在弗吉尼亚州经历的一段珍贵的复古农村生活。
——《波士顿环球报》
本书对现代人生活的价值观提出深切的反省。
——《伯明翰新闻报》
一本精采绝伦的好书……充满冒险精神,处处都在克服逆境。
——《里格菲杂志》
每个人都梦想要抛弃数字时代,反璞归真过生活。作者却真的这么做了。他在这一年中得到深刻的体验,有时则是爆笑的经历。作者以精细的观察,写出一本既深思又愉悦的著作──应该慢慢阅读,如果可能,在烛光下读它,让你的脑子停下来,让你的心安顿平息。
——汉普顿·赛兹(Hampton Sides,《鲜血、雷电与美国志》作者)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经幻想过放弃一切、回去亲近土地,就该阅读本书。作者的这段经历会让你感到美梦成真,受到鼓舞和激励。
——卡罗琳·凯托维尔(Caroline Kettlewell,《神通情人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