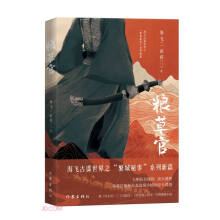崔利普什给玛格丽特的信
12月31日。日出。阿图姆-哈杜的墓室外。50手摇留声机里发出声音:我在后廊的秋千上呢。(你不过来和我一起坐坐吗,亲爱的?)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我永远光彩照人的王后,我和你父亲明天就出发回家,回到你身边。我们会乘坐北往开罗的豪华游船,在开罗城里的斯芬克斯酒店待一晚,然后坐火车回亚历山大,我们已经在那儿定了意大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的胜利者通行证,它会在马耳他、伦敦和纽约停靠,我们会从纽约搭乘最早的火车回到波士顿的你身边。1月20号你就能拥抱你的未婚夫和父亲了。
当然,我这次回来最重要的事当然就是我们的婚礼。在休息整顿之后我会回到这边进行第二次探索,去德尔?厄尔?巴哈利进行壁画的图片研究,清理古墓里的文物和珍宝。这一切都还在进行,今晚的任务就是将墓室入口封起来,让它保持被发现时的样子。然后将这个包裹寄给你。我的邮差已经到了。
亲爱的,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了。我在这里的成就,你父亲的再三祝福,全都正是我当初所承诺的。当你知道我和你爸爸又成为了铁哥们儿时肯定会松一口气(谢谢你的“警告”电报,但是你父亲在波士顿的莫名怒火在我的陪伴下在这儿从来没出现过)。不,他祝贺我取得的发现(“我们的发现!崔利普什!”他纠正道),困倦地送上他对你的爱,并不好意思地请你忽略那些他所说过的关于我的蠢话。他之前精神很紧张,被嫉妒和密谋者包围着,现在他只是很高兴我原谅他了,即使这只是暂时的,是我为那些腐蚀性的谎言所作的屈从。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你的身边了,而你也会回到我的身边。
当然,若是你正在读这封信,那就意味着我因为一些目前只能推测的原因,没能安全地回到波士顿和你的怀抱。我没有满载着不朽的功勋回来,没有将我从阿图姆-哈杜墓中带给你的这条最耀眼的铂金链子戴到你洁白的脖颈上。而且我也没能温柔地把你带到你父亲客厅的双高拱形窗下,将你为我的归来而流下的喜悦泪珠拭去,轻轻地告诉你,那个远从埃及而来印着诱人邮戳的包裹(就是这个包裹)一收到就给我。这个包裹是寄给我自己的,请你帮忙照看,只有在我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延长归期时你才能开启。
不,事情会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进行,你不会读到这封信。我会比它先到达,会在你打开它之前轻轻拿走它,全部内容都不会被看到,不需要了,这只是我自己才知道的一个预防措施。
但是,但是啊!玛格丽特,只是但是。你已经像那些恶意地希望我们失败的人一样清楚地看到,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命定的意外或者厄运会降临到我身上。所以我正冒昧地将这密封好的日志寄给你。亲爱的主啊,希望这些都能顺利抵达。
玛格丽特,如果我的敌人们的该死的触角还没有侵入到埃及邮政系统的话,你应该拿到按写作顺序寄出的三个包裹。第一个是10月10日寄出的,我那时刚到开罗的斯芬克斯酒店,脑中还充溢着我俩订婚典礼的思绪。日志条目并不是为了出版,只是和那些已出版的日志,以及已完成的部分混在了一起。大部分日志都是给你的书信,我之前都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将它们给你,直到现在。我想在波士顿将它们再整理一下。第二个包裹是我受够了酒店文具的供应,为此必须仰仗为埃及政府文物机构慷慨大方的员工时开始装的,核心的几页是写给机构理事长的。终于,我几近写满了这份漂亮的关于列托人46号印度和殖民地的日志初稿,这将是英国探险家们在高温的遥远地方的沙漠中工作,在隐藏的风险中发现的首选的日志。不要担心,这些是从日志背面撕下来的仅有的几页。这三份文件一起组成了我不争的著作——《拉尔夫?M.崔利普什和他在阿图姆-哈杜墓的发现》的初稿。
我也将你寄给我的混杂着温柔与残忍言语的信都装在里面了。七封信和两封电报,还有那封昨天被扔到我脸上的本要寄给你的电报,还有你父亲给我的电报。
我刚刚换了我的唱针,到了最后的一首,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我让一个小男孩当我的信差,我信任他。
玛格丽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将被侵蚀。风沙研磨,瓦砾掩盖,纸莎草被掩埋,油漆脱落。这里的部分肯定会被摧毁。但是有些侵蚀其实是种澄清,因为它将虚假的外表、寻常的失误、混乱及无关紧要的细节都冲刷掉。如果在我书写日志的过程中,在某些地方犯下些错误,或者没作好对我所见到的或我认为的事物的描写,好吧,我当时是想着没关系的,我可以回家以后再作修改。我会的。但是,如果我被打死,被塞进一个瘦长的旅行包里,然后变得支离破碎,我的碎片被懒洋洋地抛给海里饥饿的鲨鱼,那么,我肯定很遗憾没有对我的日志作重新编写。那样的话,我就需要一位能够吹开嚣尘,揭示像黑曜石和雪花石般鲜明、冷酷的真相的聪明且有勇气的编辑。而你将清洗掉这些侵蚀。
我们展开了这项残酷的工作,我信任你,我的缪斯幻化的执行人。你现在成了我所有成果的守护女神。这些写作是关于我的发现的故事,是我对那些质疑者和自我疑问的痛击。我像坚信自我的永生一样信任着你。我抛开所有只依赖着你,我还能依赖谁呢?如果我的身体发生任何不幸,那么当你打开这包裹读完这些内容,你就担负起了确保我和阿图姆-哈杜的名字永不消失的责任,至少为我完成这件事吧,玛格丽特。
你要监督我最后作品的出版工作,一定要用大型的著名大学的出版社来出版。让你美丽的双脚有力地跨进那些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开罗的大学图书馆和主要的埃及古物博物馆,占据书架的一席之地。还有大众出版!捂住耳朵吧,玛吉!因为新闻一经流出就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喧嚣。但等你准备十足之前,一定要把消息守住。做好我告诉你的这些,分毫不差地坚持用我告诉你的方式来出版,别给那些秃鹫留下一丁点好处。
我现在没有时间来编辑,这里的事情进展得太快了。我们明天就得离开。所以我安全抵家后会自己做这些事。但是,请允许我假定事情进展顺利而加以指导。
比如说,就现在我看着它们,肯定还有一些早期的示意图似乎还没完成。光线太暗的时候,眼睛就会被欺骗,特别是当一个人处于匆忙之中时。但是最后的绘图毫无疑问是很准确的,所以可以去作那些初步的努力。你得提炼我持续寄给你的信的内容,那些我散落在过于坦诚的日志条目里的隐私。哪些是专属于你的,哪些是献给这个日渐分离的世界的,只要你够细心,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我从一开始就无限渴望成为这样一个日志作者与你通信。公开我和你之间的任何事是毫无必要的,还有那些聚会和同伴关系。我那时很兴奋,而且理由很充分,玛格丽特,就像历史将证明的那样。我现在也有一些肆意的冥想,在四处释放出丝丝学术的气息,我的第二次猜想还留有一些失误的空间,但是一到露天就都窒息似的消失了。仔细去阅读,我请求你,一定要在私下仔细阅读,认真地编辑,然后找个打字员(叫沃农?科林斯过来),利用我在笔记本里的注释,就用最后一组,当整理关于阿图姆-哈杜的悖论时,至少我自己能理解我所看到的东西。
如果你必须因我而变成寡妇,那么玛格丽特,你也会成为我清理侵蚀的那阵风。我刚刚开始梳理资料,但是时间不够了,我也许能将主干划出来,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些,我会把你的工作尽可能变得简易些。
有序的相关资料:肯特、牛津,和我朋友一起发现的C部分,他的悲剧结尾,我们俩的相爱,你父亲的投资,气势恢宏的阿图姆-哈杜墓穴,对他的悖论颇具深度的解决方案,为密封我们的发现物推迟了归程,我和你父亲回家,我们不幸被杀,当然或者没有被杀。再不能比这更清楚了。将剩下的部分当作是一个学者早期草稿的编注烧掉。
这里的日出和我以往见过的任何场景都不一样。当太阳融入变幻之中的沙漠峭壁时,那颜色是在波士顿或肯特绝对看不到的。这里印刻着我不可磨灭的生命故事的山丘与崖壁。
最后一曲,我真的很爱这首歌。
如果说,玛格丽特,你正在读这封信,并抽泣着,被你同时失去父亲和未婚夫的双重损失吓坏了,但是又抑制着自己,紧握着手中的笔,完成眼前至关重要的工作,那我得毫不犹豫地在这里指责你,在这可怕的罪行发生之前,疯狂的霍华德?卡特——你可能几个星期前就听说了这个名字——这个半疯癫的先天走运但错误百出的家伙,他意外地在楼梯上摔倒后奇迹般地掉进了某个保存完好的小型古墓里,这个古墓是第十八朝被称为陈腐又共和的少年小国君主的墓。这个疯子因为病态的嫉妒,几个月来有好几次在吸了当地的麻醉剂之后威胁我的人,不管他是吸毒后变清醒了还是懵了。如果我在专业日志里没有提到卡特对我不间断的敌对态度和毫不节制的暴力,这种世故表现只是一种苦涩的对一个曾经伟大的探索的职业礼仪,更是一种你一直喜欢的、我惯于展现的特别的勇气。所以我一直忽视他对我和我“高贵的同门,莫名消失的切斯特?科瑞佛德?芬纳兰先生”的不断威胁。显然,要是我和你爸爸在纽约港时没有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上走下来,你完全可以断定我们是被卡特或他的某个打手干掉了,比如他的会计,一个瘦高的英国绅士,他温和的举止消弥了或者让他显得几乎不具备任何邪恶的品质——即使他施展着这邪恶,或者是他们中其他有着丑陋橙色头发的同伙,那个你最清楚不过的人。
我最美的玛格丽特,这几个月我们之间不乏误解。但是从你焦急的信件和更加焦急的沉默不语中,我知道你对我的爱如我对你的爱一般从未改变。这世上再没有比你的拥抱更让我珍视的东西。留声机里的音乐结束了,现在只有正在消失的哮鸣音。
这是我带来的几百张唱片中的最后一张了。一想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再也无法拥抱你,当你穿过花园闺房的窗户和房间时在微风中颤抖,而我再也看不到你苍白的脖颈和美丽的手臂,我被这些想法紧紧攫住,几乎写不下去了。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你会觉得我是你父亲所描述的那样的人,那不是真的我,那个在我看来一开始你所认识的我。请你像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你所看待的那样看待我,那个最让你引以为豪的人,那个你长久以来所找寻的英雄,那个你能想象到的唯一,那个一起谈论我们脚下的世界的我。请那样看待我吧,我最亲爱的。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用超乎你想象的方式爱着你。
很快就能相见了,亲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