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鹿港
十一那天早上我从观音山坐了96路公交,在沸腾、嚣张、逼仄、汹涌的人流中安然无恙地回到白城附近租的小公寓。一年一年看见这些大军从东边西边北边和南边肆虐拥过来我已经丝毫没有了起初的新鲜感,呆滞木讷地看着海水吞噬着莫名之物,再吐出莫名之物。
插进钥匙推开门我就一头栽进床铺,打了个长长的呵欠,仿佛筋骨松动起来又重新整合了一般,骨节排列的颤动刺激了耳鼓,一阵软酥之感。昨天晚上吹了一夜的海风,恐怕是着了凉,幸好有台湾面馆老板娘鲜美的三丝丸面和那杯感冒药才不至于一副病怏怏。到这里七八年了,从来没有那样感受过如亲人般备至的关怀,本来我该是热泪盈眶地感谢她的,却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喷嚏笑了场。
等我被一道热乎的光晒醒的时候,被单已经自由落体同黏糊糊的地板合为一体了,我弓着身子,像被煮熟的虾条。因为走得匆忙回得松散,窗帘也没有拉上,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射在四壁、地板和床上。
窗口外边沸反盈天,我走到阳台,鱼缸里三株鱼苗暴毙,剩下那只穿梭在浑浊的水中游弋。死去的那些突兀的眼珠仿若诅咒着什么,翻起白肚皮,一动不动,任水流将它们来回冲激。那只活着的,疲倦地忽游忽停,事实上我并不清楚它或它们在想着些什么,被圈在这个狭隘的空间里,弧形扩大的世界,短暂的记忆,每一次都宛若新生,可新生是什么,是斩断以往的一切,还是孤独的诿过。
未来遥遥无期,而过去的早已了无踪迹。
五年前当坚果同老姚分手投入我怀抱的时候我的心底像是被扎破了一个无底洞,空虚之感分秒不停地涌入,原本我以为我会亢奋、跳跃、如获至宝,但事实上是,我失去了整个世界。
阿默亦从那个时候同我翻了脸,他去了上海;不久老姚追随太宰治到日本留学,三年前卧了轨,连尸首都没能觅回;而坚果,在我最颓然的时候也北上去看雪了。我度日如年同生活打起了拉锯战,在鹭岛搭窝,在公司做小职员,单身无情人无友人的日子让我觉得似活非活,似死非死。只怪我们早已放弃了原初,踏平了底线。旧日老友今日全然无影,MSN、Email、QQ、TELnumber早就删得一干二净,逃离了生活的人注定是要奔入悲剧之中。幻影像巨大潮汐在月圆之夜将我覆灭。嗤笑、忧郁、冷漠、反感、抽搐,城市病让我拥有的只是这些。大喜大悲抵不过小情绪的宣泄。
镜子里长满胡茬儿的我仿佛在提醒着自己,蝇营狗苟地活着只会陷入更加悲惨的境遇,可那又怎样,我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此刻我想起了阿默,那个斯文、干净的模样,同我形成截然的反差。可笑至极。
1999年世纪末人心惶惶。那一年我们十三岁,对一切都感觉如此新鲜,校园电台总在黄昏散场追赶时髦播放着流行歌曲,然而红砖墙渗透出的颓废之感却又像是一种落寞的自白。拆除与重建,小县城在夜以继日地换血,换掉肝脏、皮囊,斧头一砍一根断裂的碎骨。他们说这是为了迎接干禧年和新时代。可那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想在废墟里挥舞着棍棒,提着破收录机在拆卸钢筋前放着涅槃,在旧砖墙边撒泡尿,在老树根后捣乱。夕阳和黄昏让我们瞬间变得苍老,自以为羊肠小道望穿人生轨道,可惜那不过是在盛夏提前到来的泛滥秋水。
我同老姚拿着美工刀站在巷陌的拐角,高耸的灰墙壁垒遮住的晚妆的夕阳,七时一刻,一双蓝灰色帆布鞋率先跃入我视线。白底灰绳,不沾泥屑。我把老姚往后推,自己先冲锋上阵,拇指和食指轻按美工刀握把,露出一截银白的闪光。但我只是僵持在了那里。他竟一眼也没有朝我看过来——他戴着一副沉沉的眼镜,背着四方黑布书包,眼睛一直盯着手里那本厚书籍,缓慢地翻页亦如他缓慢的步伐,似乎对这条路径的每一寸都娴熟于心,淡然、坦荡。白衬衫,黑长裤,就这样缓慢地从我视线移开,老姚劈头盖脸骂我:“你傻呀!干吗不拦住他。”我默默地念叨着方才余光瞥见书脊上的那几个字,“列夫托尔斯泰”、“复活”。我把手上的美工刀往地上一扔,架起老姚的肩膀说:“以后我们不干这种勾当了。”夕阳在最后一刻耷拉下了脑袋,小城陷入黑色的恐慌之中。
在同阿默相互熟稔之后每每谈到这段事情总不觉捧腹大笑。阿默说他能想象我们那副模样一定像足了四处游荡的小武。穿梭在这个小城最萎靡不振之处,然后同荒草一般芜杂地生长。反倒是我记不清当时老姚为什么要跟我混迹街头,他有个有钱的爹,有个美艳绝伦的年轻后妈,还有大房子住;而当时我们家租在废弃修理厂的危楼上,那像极了个乱坟岗,很多工人被搅拌机搅得血肉模糊就同水泥一道拉出来凝固在地上,母亲对生活从来就没什么指望,她每天喂了大黄就去河边捡点菜叶,然后操起细棍就打我,毫无缘由地打,哪怕我只是趴在床上睡觉,她也能用小木棍抽打得我皮开肉绽。不过那都是小学时候的事情了,我上初中以后母亲就对我恭敬多了,因为我已经比她高了,力气也比她大得多,她知道她打不过我,但可以让我慑于她的威严。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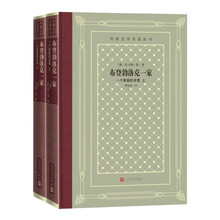

——《一月气聚或离散》
“直到青苔上到我们的唇上,且淹没了我们的名字。”原来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也在老去。可是,为什么夏天还没有过去?
——《住在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