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眼窝
在酒蓝色的洋面,我颠簸了十九个日夜,直到昨天登陆。遭受狂风和海浪的击打,把我从俄古吉亚海岛一路推搡-现在,命运把我带到此地。
——荷马《奥德赛》
多年前,在我仅养两只猫的时候,我总爱说,如果我再收养第三只猫的话,我会给它取名叫“猫主席”,简称“主席”。
“不要这样看我嘛,难道这个名字不可爱吗?”每当朋友们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时,好像我是个疯子似的,我总是这样说,“小猫主席”。
这玩笑有两层意思。一是名字本身很有趣,二是我想收养第三只猫的念头。如果不是因为与一个我认为肯定会嫁给他的男人共同生活了三年,我可能绝不会做出收养两只猫这样重大的决定(对二十四岁的我来说,这决定事关重大)。那个男人叫乔治。最近我们分手了,我获得了猫咪的监护权。一只叫瓦什提,温顺、漂亮、毛茸茸的纯白色猫咪;另一只叫斯嘉丽,高贵但有些情绪化的灰色斑纹猫。我很感激我的两个“姑娘”每天陪伴着我,但同时也痛苦地意识到,她们俩对我的新单身生活可能会造成潜在的困扰,那种在我认为自己和乔治会永远在一起时,从没想过的困扰。
我住在一个朋友的闲置房间里,我想存钱找个能租得起的地方,可是,我永远也不会住到一个价格合理但禁养宠物的地方。此外,我也不会考虑和一个对猫过敏的男人交往。我在一家非营利组织-迈阿密-戴德联合劝募协会-工作,负责组织一些志愿者项目。因此,每个月底我银行账户里的存款不会超过五十美元。尽管如此,猫咪的例行疫苗注射以及受伤或生病的治疗费用都得我一个人支付,不论这些费用是否会影响我的开支。
“不要提什么社会影响了,”我的密友安德里亚会说,“我的意思是,你只有二十四岁,而且又是独身,你能收养多少流浪猫呢?社区里的孩子会叫你老寡妇库珀,然后扔石头砸你的窗户,嘴里喊着:‘那是老寡妇库珀的家,就是那个养猫的女人。她是个疯子……’”
我知道她的话没错。我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人。以我目前的状况,要想养第三只猫实在是荒唐,无异于幻想着如果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大奖要买些什么。
在我和乔治分手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了帕蒂的电话。她只比我大三岁,是为斯嘉丽和瓦什提看病的那个诊所新来的兽医。她向我讲述了一个很长很悲伤的故事。如果有哪家电视台叫“猫的一生”的话,这个故事非常适合被其拍成剧集。
帕蒂说,这只刚满月就没爹没妈的流浪猫,被人遗弃在她的办公室里。它的眼睛受到严重感染,需要做双眼切除手术。把猫送到她办公室的那对夫妇不要它了。帕蒂收养名单上的人没一个想要它,就连先前对收养残疾猫表示兴趣的人也不愿收养它。似乎没有人愿意面对这种特殊残疾。我是帕蒂打电话询问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她能想到的最后一个有可能收养这只猫的人,否则……
她没把话讲完,也没必要讲完。我明白几乎不会有人愿意收养一只盲猫,他只有等待生命的消亡了。
不要!我脑海深处响起希腊合唱队的歌声,警告我不要收养。是的,这故事是很悲惨,不过,说实话,你对此无能为力。
我是个书痴,喜爱读书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我知道文字能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力量。让我看到失明、遗弃、没人要、孤儿这些字眼,并与之抗争,就犹如让某人带着玩具步枪上战场一样。
不过,尽管我不能做出同样冷静的分析,我还是意识到了自己内心里希腊合唱队的理智。于是,我便回答说:“那我去看看他吧。”我停顿了一下,“但是,我可没做任何承诺哦。”
我应该说明的一点是,在此之前,在收养宠物时,我从没采取过“见见再说”的态度。我从没想过要先见见宠物,看它是否“特别”或者我们之间是否有某种特殊的缘分。关于收养宠物这事儿,我认为就像抚养孩子一样。孩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无论其个性如何或有什么缺点,你都会无条件地去爱他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父母收养了无数只狗,几乎都是流浪狗,或者在以前的主人家受到虐待的狗。有的狗很难训练它们在指定的地方排便,有的狗咬坏了地毯和墙纸,有的狗不停地在篱笆下刨土,有的狗在受到惊吓时偶尔还会咬人。我收养斯嘉丽和瓦什提前后相隔了一年,她们是从我朋友那里收养过来的。朋友们发现她们时,生下来才满一个半月,流浪在迈阿密的街头,饿得半死,浑身疥癣,通体是跳蚤和脓疮。我还没见到她们时就决定收养了。我第一次见到她们那天,就是她们跟我回家的日子。
第二天下午,在开车去兽医诊所的途中,我觉得自己不够诚实。帕蒂也许没有意识到,但是当我说“那我去看看他吧”这句话时,我很清楚自己想说什么。我的意思是,我现在真的不能收养第三只猫了;然而,如果听了这么悲惨的故事之后再说“不”,我会觉得自己太差劲了。所以,我给自己留了余地,以便摆脱收养的诱惑。
“我们必须收养他。我们得让他住到这里来。”这是头天晚上我对室友玛丽莎讲了盲猫的故事后,她做出的第一反应。她说的“这里”是指她那套位于南海滩海滨的两居室。我为了存钱找自己的住处,暂时借住在她那里。我们分摊水电费、伙食费和其他房屋开支。但是,玛丽莎人长得漂亮,又是财产继承人,在我生命中这个关键时刻,盲猫的出现对我来说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然而对于她则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玛丽莎不用为高额的兽医费用烦恼,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自己和一窝宠物(三只!)的住处,或者遭遇没人约会的窘况。(我似乎已经听到那些自己想象出来但从未见过的-更不用说约会了-男人们之间的谈话。嗨,朋友,她是多么聪明、多么可人啊,而且还富有情趣-但是她养了三只猫!那太糟糕了,朋友!)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收养这只猫的合适人选。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有特殊需求的猫,但我还无法想象,那会是些什么样的需求。如果他永远都学不会行动和自理,那该怎么办?如果我的另外两只猫第一眼就讨厌他,让他一生都不好过,那该怎么办?如果我不能很好承担照料他的重任怎么办?我甚至连自己都照顾不周呢。此刻,我正寄人篱下,这就是我不能照顾好自己的最好证明。
玛丽莎用了“我们”这个词,一下子给了我勇气。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孤单一人。我的聪明小脑瓜里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想法:我把猫咪带回家,如果我没有能力抚养他的话,玛丽莎总能……
“当然,最终决定人是你,”过了一会儿,玛丽莎又补充道,“因为你搬走时,他是要跟你走的。”
首先,我同意要去看看这只猫咪。此刻,我正开车急匆匆赶往兽医诊所。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一种负罪感。如果我不收养他,也许就没人会这么做了。只要一提到动物,大家都知道我很容易动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志愿者,每到周末,我都会到迈阿密的许多动物收容所里工作。当我和乔治还住在一起时,我回到家时总是两眼泪汪汪的,用各种理由恳求他考虑收养那些若没人领养就要被施以安乐死的猫狗们。我唯一一次卷入法律纠纷是在大学时期。那一次,在我们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实验研究中心外面的抗议集会上,我被拘捕了。记得小时候,流浪猫狗们会一路跟我到学校,因为我见到他们就会把饭盒里的食物都给他们吃,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午饭。
当我驾车开进兽医诊所外的停车场时,我有点严厉地对自己说,正是这种模糊而不成熟的想法,这种完全不顾后果的做法,使自己沦落到目前这种状况-经过多年苦心打拼,自以为未来已经稳定有靠,结果却依然一文不名,孑然一身。
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试图制造愤怒情绪。我想让自己相信,自己只不过非常生气,并非胆怯。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闷热潮湿。银色的热浪犹如幽灵般从百货中心前的人行道上升起,兽医诊所就在那里。我走进诊所,前台接待员热情地向我问好,并向帕蒂通报,说我到了。帕蒂从前台后面的门里探出头来,语气轻松愉快地招呼道:“到后面来吧!”
我跟着她经过一排排关着猫和狗的笼子。以前我见过这些笼子,但从来没有特别在意过。我一直认为主人只是将它们临时放在那里,让兽医照看一下,最终会把它们带回家的。这是我第一次感叹,想知道它们当中有多少其实是无家可归的小东西,正在等待着像我这样的人来收养它们,但最终是否有人决定收养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经过一条镶有木质护墙板的狭窄走廊,来到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检查室。帕蒂为我打开了门。检查台上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塑料盒。“你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她说道。我走了过去,朝盒子里看去。
我的第一反应是他竟然如此娇小孱弱。我另外两只猫也是在这么小的时候被我收养的,但是我完全不记得四周大的小猫到底会有多小。他一定只有几盎司重吧,蜷缩成一个小小的绒球,躲在盒子最远处的角落里。我感觉自己的掌心便足以放下这个毛茸茸的软球。像所有幼猫一样,他那一身黑毛似乎不愿意在身上平顺伏贴,而是犹如起了静电反应似的直立起来。他的双眼用细线缝上了,脖子上挂着一个圆锥形塑料颈圈,为了避免宠物自己把缝线扯掉。
“我把他的眼睑缝上了,”帕蒂说,“这样他的眼窝看上去就不像是两个空洞,而是让人觉得他始终都是闭着眼睛。”她说的对。他眼睛上那些×形的缝线,让我想起了儿时卡通片里醉鬼或者死人的眼睛上总是画着一个×。
“喂,你好!”我轻声说。我往下蹲低了身体,这样我和小猫便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听上去就不会觉得太响,也不会吓到他。“嘿,小家伙。”
角落里那只黑色绒球舒展开身体,迟疑不决地站了起来。我试探性地伸出一只手,这只手看上去突然显得异常硕大。我把手放进盒子里,轻轻刮了下盒底。那只小猫慢慢朝着声音的方向走来,由于塑料颈圈的缘故,他的脑袋来回摆动着。他的鼻子碰到了我的一根手指,然后好奇地嗅了起来。
我抬头看了看帕蒂,她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把他抱起来。”
我小心地拎起猫咪,轻轻地把他侧身抱在胸口,一只手托着他的屁股,另一只手搂着他的肚子和前腿。“嘿,小家伙。”我轻声唤道。
听到我的声音以后,他转过身来,把前爪搭在我左肩上。他的前爪是那么小,陷在我身上薄毛衣的毛线孔隙里。他挣扎了一下,我可以看出他想整个身子爬上我的肩膀。但是他的爪子实在太小,没法抓得很牢。他只好放弃,然后又扭动了几下,不顾塑料颈圈的阻碍,把脸尽可能凑到我的颈脖上。他试着用自己的脸蹭我的脸,不过,我感受到的只是那个塑料颈圈的摩擦。然后,他开心地咕噜咕噜哼了起来。从那个锥形塑料颈圈里传出的声音显得非常大,他仿佛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型引擎。
我没有期望双目失明的他能够表达多少情感,我想这或许就是那些拒绝收养他的人心中的担忧和害怕吧。如果不能从宠物的脸上看出爱、感受到情感的话,那它就相当于家里的一个陌生人。
不过,当我抱着他的时候,我意识到人们流露感情或思想靠的不是眼睛,而是眼睛周围的肌肉。肌肉牵动眼角向上或向下,眼角皱起表示开心,眼睛眯成一条缝表示愤怒。
虽然这只猫没了双眼,但是他的眼部肌肉完好无损。我从他眼部肌肉呈现的形状可以看得出,如果他有眼睑,他也会像我另外两只猫一样半闭着眼,露出我十分熟悉的表情:一种无比满足的表情。他舒心地滑进我怀里的这一动作就已经表明,不管他以前经历过什么,无论他有千万种理由担心现实会与期望相反,在这只小猫的内心深处,他知道终归会有一个可以让他感到温暖与安全的所在。
此刻,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哦,谢天谢地。”我轻轻把他放回盒子里,然后在我的皮包里翻到了一张纸巾。“把他裹起来,我现在就带他回家。”
帕蒂坚持要小猫在她那里再多留几天,因为她想再观察一下盲猫眼睛上的缝线,担心他会感染。此外,她还希望小猫能再长大些,否则没法吃固体食物,还会被另外两只成年猫抢食。“你过几天再带他走吧。”她承诺道。
我终于能够得到我的猫主席了,但是这个预设的名字似乎不再适用。“你应该叫他眼窝。”玛丽莎建议。
“这名字太糟了吧!”我大叫,“他不叫眼窝。”
她善意地耸了耸肩。“对我来说,他永远都叫眼窝。”
我给斯嘉丽和瓦什提取名时,几乎没费什么劲。斯嘉丽来的时候已经有名字了。她是一只流浪猫,我的机修工发现了她,给她取名斯嘉丽,因为起初几天她脱水严重,常常昏过去。瓦什提的名字取自《圣经》中的一位波斯皇后。她拒绝为她的丈夫波斯国王及其醉鬼朋友在宴会上跳裸体舞,因而被驱逐出王宫。她是我知道的最早为女权主义献身的人。我的瓦什提从一只仅剩半身毛的瘦骨嶙峋的可怜猫咪,出落成一只异常美丽的长毛猫,看上去很像波斯猫。不过,这纯属一个令人欣喜的巧合。
我不想给这只新来的小猫取些听上去矫揉造作或者很明显双目失明的名字(比如“Ray1”和“Stevie2”,这些是很多朋友好心建议的名字,对盲猫来说确实很合适)。不过,我也不想把一些很严肃、很有预示性的东西强加在他身上。他永远都是只盲猫,这将是他生命中无法回避的事实。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也不希望让他的一生里只有“失明”二字。
随后几天里,我经常去兽医诊所看他。他那短暂的生命已经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令人困惑。我希望在他和我回家时能有熟悉和安心的感觉,哪怕只是熟悉我的气味和声音也好。
但是,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有许多担心。他现在属于我了,这已不能反悔。但是,我想亲眼看看他如何四处走动,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以及学会如何应对这个世界。
因此,每天下午,在我完成了一天工作后,我都会到帕蒂的办公室稍事逗留。她会把小猫从笼子里抱出来,放到检查室里,让他自由活动一会儿。大多数时候,我就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他。
我已经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探险家。他脖子上那个塑料颈圈,仿佛是游侠骑士穿越敌人阵地时手中的盾牌。颈圈太重了,压得他的脑袋无法完全直起来,但是他的鼻子几乎一直贴在地上嗅来嗅去。检查室非常小,他嗅遍了每一个角落。当他撞到墙壁或者桌子时,他就会用小爪子警觉地碰碰,就像一个工程师在测量面积和厚度。他唯一试着攀爬的是房间角落里的一把椅子,而对面角落里一株很大的盆栽看上去也很有吸引力。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说“不”。我不希望他弄得一身泥土,或是不小心把植物给毁了。
终于,再过一天猫咪就要回家了,但他还是没有名字。“眼窝”似乎很有可能就会被默认为他的名字了。
他需要一个名字,需要一个合适的名字。于是,我试着把他想象成故事中的某个角色。他的生命像许多精彩故事一样已经开始,但还有无数磨难和艰辛,以及意想不到的逆境和无数障碍。
但是,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故事里的一个角色,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创作者。即使他失明了,但我肯定他也会想象出许多东西来认识他周围的世界。昨天那地方还没有椅子,今天怎么就神奇地出现在那里,挡住了我的去路,这如何解释?椅子是什么?为什么要有椅子?椅子是怎么做出来的?每当我想着要做某些不允许做的事情时,无论我多么轻手轻脚,养母准会知道。她怎么会无所不知呢?当他第四次试图爬上角落那株满是泥土的大盆栽时,我也情不自禁地第四次喊出了“不”。猫咪一脸疑惑。他当然没法分辨“无声”和“无形”。他一定在想,我的步伐如此之轻,她怎么总能发现呢?
当你收养宠物的时候,你以为他会成为你人生故事里的一个配角。但是,我开始意识到,我将成为这只小猫故事里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一个努力奋斗、充满自我怀疑、收养着三只猫的单身女孩,变成了一尊无所不知的永恒之神,仁慈善良、神秘莫测。
我看见他尝试着想穿过检查室。对我来说如此狭小、如此熟悉的检查室,在他眼里是那么宽广、那么陌生。他在桌腿和一个装水的小碗间进退两难。就在这时,他一下摔倒了,面朝水碗一头栽了进去。我一把将他拎了出来,轻轻哼道:“乖猫咪,乖孩子。”然后,他咕噜了几声,似乎很开心上帝又一次眷顾他。无论他有多憎恶盛水的碗,或者对椅子的高度判断失误,或者撞到了桌腿上,他都坚持不懈地尝试着。
他似乎在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到另一边去。
他不仅仅是探路英雄,也是英雄和神话的创造者-神话一直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是用来解释神秘事件的。他就是奥德修斯,他也是那个想象出奥德修斯的盲人讲述者。即使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却能够从宏伟的角度审视人生和生命。
这时,我知道自己的猫咪应该叫什么名字了。
“荷马。”我大声说道。
他用一声响亮的“喵”回应了我。
“很好,你就叫荷马了。”我很高兴我们一拍即合。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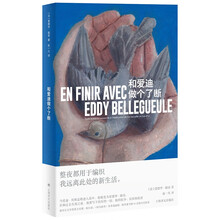
——《图书馆杂志》
爱猫者无法抗拒的杰作。作者在生计与爱情间的挣扎令有类似经历者深深共鸣,进而感染了所有面对挑战、逐渐成长起来的人们。
——《书单》
一个关于爱与生命,催人泪下的故事,真实存在于宠物和主人之间。
——《佛罗里达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