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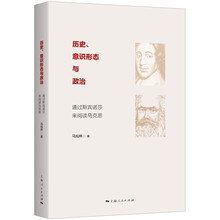
如果说20世纪之前德意志法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到观念论哲学逻辑的支配,那么从20世纪开始,则注入了一些新的要素。法哲学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专业化,另一个是多元化。他们逐渐丧失了从总体上和宏观上把握法律的能力。此种对于法的碎片化理解直接促成了一些争锋相对的“立场”。这些立场在德意志法哲学发展之初是不曾显现的。它们各自立足于自己的视野而对法进行了一种“去总体化”的解构。在这些立场之中,突出地表现出以下四种路向:一是技术路向,二是政治路向,三是自然法路向,四是社会学路向。本卷所选译文献便围绕着这几种不同的法哲学进路,它们同时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思考法律的几种基本方向。
法律形式性与选择自由——道德视野下的耶林建构主义
[奥]亚历山大·索梅克(Alexander Somek)著
姚远 李丹阳/译
如果把作为概念主义最极端表达而闻名的耶林法律形式性观念视为一种权利理论,那么这一观念便有了意义。通过这样一种视角,我们就能理解耶林晚期的方法论自我批判,即他通过反思权利体系所赋予的选择价值来缓解概念建构主义的倾向。
计划的意义
罗马法教授鲁道夫·冯·耶林主要因为两种不同的法律理论而闻名遐迩。人们通常认为第一种理论代表“建构主义”的最极端表达。很多人又认为他的第二种理论——法律被描绘为人类目的之理性追求手段——代表了与前一理论的决裂。这第二种理论仿佛标志着与第一种理论的决裂。它早在1861年发表《论民法学建构》(重印于1884年,页6-17)时就已经出现了。
在下文的论述中,我将着力于耶林第一种理论的最重要方面,也就是他的法律形式性观念。丰富的二手文献引证,参见:索梅克,1992年,页128-148。 然后我将提请读者注意耶林作品中的一种潜在连续性。鉴于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看到,看起来与最初那种法律形式性观念“决裂”的东西至少在某一方面也是该观念的结果。
法律的普遍形式
耶林的法学规划主要见于《罗马法精神》第二卷第二部分(耶林,1858年)中讨论法律推理的一个大师级章节和他的论文《我们的任务》(耶林,1857年)。他着手探索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给了法律在外行民众眼里如此奇怪的外观。他认为,可以在被他称为“法律技术”或法律推理的技艺(古典意义上的“ars”或“techné”)的东西中找到理由(耶林,1858年,页322、页325、页377)。尽管耶林似乎只是试图说明“法学家”的视野与外行人的视野有怎样的区别,但显然他希望阐述,在以法律专业技能及其显著“技术性”风格为认识媒介的社会中,人们如何认识特定情况下何谓法律。既然这样一来,此处的重点在于认识何谓法律的法律方式,那么就没必要区分法官、律师甚或这里更重要的法学教授的各自视野。 在这样的社会——众所周知是“现代”社会中,法律技术标志着认识法律的模式。该技术存在与否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
从耶林的论述中基本上可以得出,在他看来法律技术是普遍性的东西(耶林,1858年,页323-325、页376)。法律技术首先出现在古代罗马法里,这一事实纯属历史偶然。耶林好像是借用爱德华·柯克的观点,主张法律技术包含着历代的智慧因而包含着积累起来的经验(耶林,1858年,页331),但该主张很难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性命题。不过,假如我们把这样一种积累过程理解为发现唯一普遍法律技术的历史语境,那么就没有矛盾了。 就像数学定律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一样,法律分析的规则也是如此。那么,耶林还声称法律技术并非“外在于”法律的概念,就毫不奇怪了。相反,一旦法律体系达到某种程度的复杂性,技术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否则,恐怕法律体系将会土崩瓦解。
因为法律技术反映了社会中对特定情况下何谓法律进行权威性认识的模式,故而法律技术也影响到法律实际上是什么。法律体系对于法律的指涉方式,为法律的实体赋予了一种技术形式。形式不是异在于法律的东西,按照耶林(1858年,页353)的看法,形式是在素材之中的。 它是法律所内在固有的。耶林说,使得外行人无法掌握法律的不单是那一大堆法律素材;外行人其实是因为“素材的种类”(《素材的技艺》:同上,页325)才感到难以理解法律。这样一来耶林就强调,被人们作为“法律”来沟通的东西承载着技术的烙印。从这里可以得出,法律专业技能不取决于或源自一头扎进素材所表达出来的诸细节。毋宁说它是对技术的一种训练有素的掌握。
吊诡的是,这意味着技术不仅把法律沟通与有关世界的其他人类谈话方式(比如哲学)分离开来,并且也把它与习惯法素材和制定法素材本身分离开来。关于法律是什么,掌握法律技术的人“所有时空下的真正法学家说着同样的语言”(耶林,1858年,页326)。 比起特定时空下的对法律实体具备大量信息的人有趣的是,这种指涉何谓法律的特定模态便把法律体系与其实体分离开来。该悖论将伴随着我们对耶林法律形式性观念的考察。 知道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