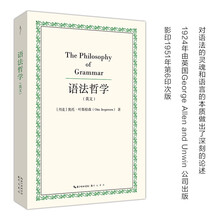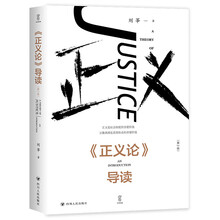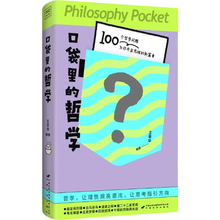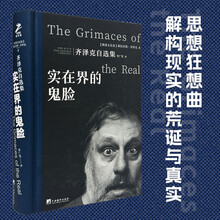《<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
二、《吕氏春秋》的引用、阐释与接受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秦汉时期两部体制宏伟的杂家著作,诸子中与道家关系密切且引用《庄子》最多者,莫如这两部书籍。它们在构建各自的学说体系时,都对《庄子》及其文学有较多的采纳、接受和传承,并作了某些新的阐释。这里先谈《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由秦相吕不韦(?一公元前235)挂帅组织其门客集体完成的一个“重大项目”,成书于“维秦八年”,即秦灭东周后的第八年,亦即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①,形成了由十二纪、八览、六论3部分组成,共160篇,约20万字这样的皇皇巨著,是汉代以前字数最多、篇幅最长、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结构体系最为严密的一部大作。这部大作“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②,是一部以阴阳家、道家、儒家及墨家学说为主,兼采法、名、兵、农、医等各家学说,集先秦诸子精英之大成的杂家著作,甚至可称其为杂家之祖。其“采精录异,成一家言”⑤,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欲为即将诞生的大帝国立典、立则而产生的,是一部为秦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而编写的完备的王政法典、治国纲要和百科全书,具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教育、文学、艺术、农学、医学等各方面的价值和文献史料学价值。由于吕书,法天地,通古今,杂取博采,集其精英,卓然自成一家,所以高诱在序中称其“大出诸子之右”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
吕书采用最多的是道家学说,尤其崇尚道家的哲学思想,主要采纳了其重道守柔、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因性任物、超然物外、贵生轻物、重己养生等思想观点,并且以“法天地”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视为全书的主脑和灵魂。其所采道家学说中,又以《庄子》为最多。书中直接明确引用《庄子》的,主要见于《本生》《贵公》《贵生》《功名》《当务》《精通》《诚廉》《去尤》《听言》《慎人》《必己》《下贤》《观世》《慎势》《精谕》《离谓》《应言》《离俗》《适威》《长利》《知分》《审为》《求人》《博志》《有度》等篇。例如,“庖丁解牛”(《精通》),“材与不材”(《必己》),“列子拒粟”(《观世》),“诸贤让王”(《贵生》《离俗》《审为》),“孔子穷于陈蔡”(《慎人》)等著名故事皆采自《庄子》。据王叔岷详检精核所作的统计,吕书直录明引《庄子》(包括佚文)的,“共五十余条”①。此外,像“天道圜,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圜道》),“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贵当》),以及“八观六验”“六戚四隐”(《论人》)等著名观点,还有像《必己》对“真人”的新阐等,也都脱胎于《庄子》。当然,吕书对道家学说也并非全盘接受,它扬弃了其逃避现实、冷漠无情、不思进取、与世敷衍等消极性,在《当务》篇中甚至还站在儒家立场上讽刺庄子学派的偏激说法。
《吕氏春秋》较多引用《庄子》,重在阐发庄子的思想,将其纳入自己的“一家之言”,这主要属于哲学阐释的范畴。关于吕书对庄子思想的阐述、发挥、补充、修正、规整、继承及相应的阐释方法,方勇的《庄子学史》论之甚详②,可以参阅,这里就不多言了。可以说,这种大量引用的本身,也是对《庄子》文学的接受和传承,只不过是按照他们的阐释方法,将其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罢了。其做法,一是在引文或前或后加上阐释者的话语作为规定的意义指向,将引文纳入其特定的语境之中,使朦胧多义的庄子寓言按照阐释者的意愿呈现其特定意义。例如,《精通》篇引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将其和“养由基射兕”“伯乐学相马”等放在一起,前有类比引导,后有“神出于忠而应乎心,两精相得,岂待言哉”的结论,在此语境下,这一颇多意蕴的著名寓言,所凸显和强化的只能是该篇所谓“精通”这一主题思想。又如《精谕》篇引用《庄子·田子方》中“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的故事,文章开宗明义就指出“圣人相遇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在引述此事后又加以议论:“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这就使一则原本讥讽孔子在得道者面前无话可说的寓言,赋予了圣人精神相谕、不用言语的新意。诸如此类,都可以说既是思想阐释,同时又是文学阐释。这与韩非那种改造、扭曲甚至故意歪曲的阐释接受显然有别,即使郢书燕说,但无论如何毕竟还是较忠实于文本的意义解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