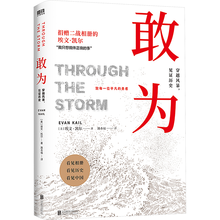《阳光灿烂:60年代生人的青春祭》:
第一章
每一次拐弯起初都是缘于逃避
天亮前倾下的雨水,在小镇坑洼不平的街道上反射着刺眼的阳光。时近晌午,没有风,有点热闷。
少年穿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下身是铁灰色的卡其布,都刚洗的,干干净净。班车老不开,师傅还在旁边的国营旧州饭店里吃蒜苗炒肉呢。少年却也不敢走远,忽而瞅见车窗外壁那大块呕吐物的痕迹,他隐约觉得脊背在过敏似的发痒,遂想反过手臂去挠挠。
这时,母亲在半途中截住儿子的手,并轻而易举将其掳在她自己那粗糙、宽大的手掌心里,接着用另一只手摁了摁。他手指患关节炎,到了冬天又肿又痛,指根处还有一排淡黄的茧壳。
“好喽,今后不消再受苦哕。”妇人说。
觉察儿子害羞似的不自在,抑或说不大耐烦,母亲便松了手,可转而又在少年肩头和胳膊的衣裳上拍打几下,黏了蛛网或草丝儿什么的。这倒是她经常性的动作。
车喇叭终于响了。“要多跟人家讲话。”母亲还在哕唆,“出门去,可比不得在家里。”少年一声不吭,依然那副木讷、漠然的样子,他从小就这样。只是,与以往不同,这一回他心里充满了欢欣之情,他意识到一个光明、希望和快乐的世界正在迎候着他。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我要走了!从今往后,我再不会在父母眼皮底下让他们心烦,也再不需要听他们唠唠叨叨。
少年也明白,稀里糊涂地他为父母争了光。除了节衣省食供他读完四年书,他们将再不用操心憨儿子今后的生计。
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出远门。
从江边到省城,辗转、颠簸近七百公里,第三天,天已黑尽,脏兮兮的东风客车车头往左一拐,进了一个大院。这里是西站,滇缅公路的起点。8年后,这里将耸起云南第一座交叉三层的城市立交桥。少年没有见到学校来接站的人,事后得知主要是班车晚点的缘故。一路上受托顺带照顾他和另一个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女娃娃的,是一位他不熟悉的县城里的女老师,她在车站跟他们分手。她要赶到某个地方去拿票,明天要搭火车上北京。
环城北路——如今改叫一二一大街了——路灯黄怏怏的,车和行人都不算多。沿右首的人行道,少年一个人徒步往前。他还不大认识公交车这东西。行李,一个铺盖卷,一大团,不过不重,反倒是那只花楸木箱子让他手指酸麻。因为那形如括号的铁襻儿不好抓握,不得不左手右手来回地换。里面实际没装多少东西,除两三件衣物和床单之外,就几《阳光灿烂:60年代生人的青春祭》,其中一本跟植物和科幻有关,作者好像是叶永烈,另一本是竖排繁体版的《聊斋志异选》,还有日记本。要么,箱子沉是因为刚做好不久,那树汁还没有完全挥发的缘故?它是父亲和哥哥伐倒一棵花楸树,抽时间赶出来的,还散着幽幽香气。那是材质本身,跟涂在木面上那层清光漆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这是他平生拥有的第一只箱子。整整20年过去,如今它还在,就躺在客房地板的一个角落里,里面空空,然而,它仿佛他的前世,或者说其中藏着他人生最初17年的清静、自在和混沌,那是一整箱他个人的古代史。清光漆的味儿早已散尽,只是那花楸木的清香隐隐犹在。
“夹江之山脚,阔者二里许,狭者江深山陡,径亦险隘,始无田,深箐丛杂,野夷星居,刀耕火种,迁徙无常。”“梅花一开以纪年,野靛花十二年一开以纪旬,竹花六十年一开以纪花甲。”康熙年问那册《江边记往》所记述的,便是少年澜沧江边的出生地。在他出生前的数年中,父母携着哥哥离乡背井,先后徒步进入滇西大峡谷,当时尚未通公路的一片化外之地。这里属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气候,阳光辣如火焰,雨水凶猛而明亮,鸟兽蛇虫远比人多,星星比灯亮,绿得发黑的树比房子高。
在这样的偏乡僻壤,当年我们的男主人翁并没有认真地做过啥子大学梦。没有多大动力,也没什么压力。对江边人来说,仿佛一棵草一棵树似的活下去就很好了,倘若自己的娃娃能考出去,那纯属天上掉馅饼般的意外,而没考上才属正常的。几十年过去,大抵也还是这么个情形。
那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临考半年前,江边少年执拗地要报文科,这在周围人眼里,略有狂妄之嫌——不过也更像是自暴自弃,或者说故意跟学校找碴?因为学校不开文科班。不成文的说法是,报理科,上不了本科可退而选专科,专科进不了还有中专和技校什么的,而文科大抵只能背水一战,几乎就是自绝生路。
当然啦,他喜欢地理,他语文成绩也不错,写峡谷风景的作文得过表扬,可数理化成绩却一直不怎么样。理科中他最头痛的是数学,最感兴趣的是生物,而生物课在学校里还没有正式开,也没列入高考科目。当然啦,原因不仅仅如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