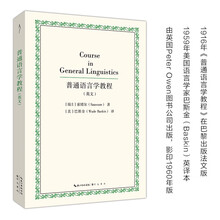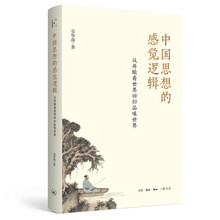《裂变与传承:儒学思想的现代诠释》:
依我看来,在科学方法论方面所产生混乱的最后根据是实践概念的衰亡。实践概念在科学时代以及科学确定性理想的时代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因为自从科学把它的目标放在对自然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因素进行抽象分析以来,它就把实践仅仅当作科学的应用。但这乃是一种根本不需要解释才能的“实践”。于是,技术概念就取代了实践概念,换句话说,专家的判断能力就取代了政治的理性。
于是,他援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区分,根据古代诠释学尤其是法学和神学的实践,特别强调应用功能在诠释学中的根本作用。应用并不是理解发生之后附随的、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的活动。没有应用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理解。所以,理解的过程也就是应用的实施过程,要进入到深刻的理解状态,就必须要把解释活动中所面对的普遍意义应用到具体的情景之中,在创造性的诠释里生发出新的内容来。由此,伽达默尔创造了“效果历史”的概念。他指出,因为诠释学的见解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知识或抽象的科学原理,它是离不开特殊情景的,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实践性学问,所以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效果,“应用绝不是把我们自身首先理解的某种所与的普遍东西事后应用于某个具体情况,而是那种对我们来说就是所与文本的普遍东西自身的实际理解。理解被证明是一种效果,并知道自身是这样一种效果”。这样,理解就是应用的过程,就是产生“效果”。因为应用不是僵化的、凝固的,而是穿梭在普遍与特殊、过去与当下之间,不断生成着新的意义,并对已有的理解产生连续的撞击和刷新。伽达默尔认为,这一效果历史意识呈现了一种开放的逻辑,其问题视域是随着应用的层面和实践的范围而不断变化的,永远都有新的问题产生。这既符合精神科学的本质,也表现了诠释学无终极性的真理观。
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追溯和阐发,意在复活一种特定类型的实践科学。这门科学既不是先验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纯粹知识,也不是经验感知意义上的操作技能,而是致力于人类生存价值的探寻、并且是把理论和实际统合起来的特殊学问。实践智慧没有普遍规则可以遵循,也没有一定的方法和门径,完全要靠在具体的实际情况中去不断地摸索,所以它构不成所谓的方法论,甚至不成为一种确定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诠释学并非只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或是标明某类特定的科学。它首先指的是人的自然能力”。这种能力因为近代科学方法的极度膨胀而遭到了遏制,实践智慧也日益被忽视。随着用科学概念和演绎方式全面取代实践过程之中的种种特殊性,实践智慧的应用也被简约化,或者划归到科学技术的应用类型中,实践的丰富性因而狭窄化为可操作的技术性。这样,以实践智慧为本质内容的人文科学也就丧失了古已有之的尊严感,而不断地遭到质疑和轻忽,日渐被边缘化了。伽达默尔认为,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科技至上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及其诸多后果,只能靠重新恢复实践理性的权威来救治,用实践智慧来矫正和有效地控制科技应用的盲目发展,裨使人类不至于茫茫前路无归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