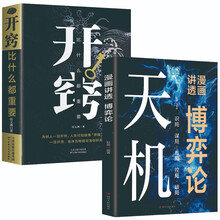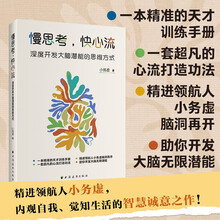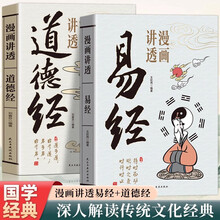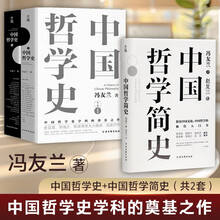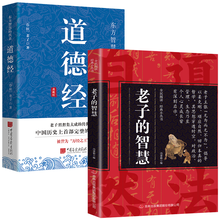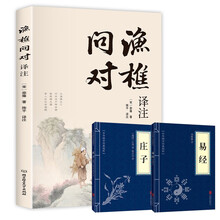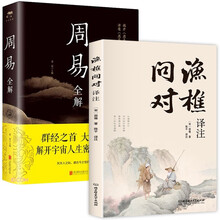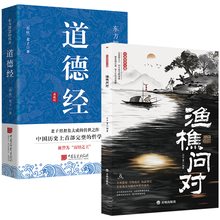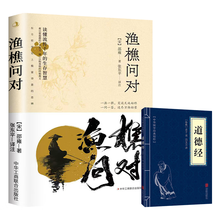《章裁集》:
——卫礼贤、花之安的《孟子》译本研究/任防··浅谈池田大作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诠释/胡藤……“东洋”:明治日本所想象的共同体/[日]加藤真平 “天籁”之后的一段文字是讨论人世间的大言与小言,这些大言与小言,其频率与表现形式都是极其不同的。再接下来讨论儒墨之间的是非之争,其声音与天籁之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声音不仅仅是在节奏上与乐器发出的美妙乐音不同,更主要的是他们用语言表达出的一些观点、思想,与“道之出口,淡乎其味”,道之入耳,“听之不闻”的“希声”相比,都是杂音与噪音。当然就不可能是“天籁之音”了。接下来讨论的“言非吹”,言未定而有所待,就比较明确地揭示了由诸子百家用自己的理论语言建构起来的所谓“真理”,其实都不具有真正稳固的根基或自足性,它们必有待于“道”。“道隐于小成”,是指人类的根本真理被人类阶段性的文明成果所掩盖。
言隐于荣华而有是非,其“荣华”亦即老子所批评的“道之虚华”,亦即儒墨等思想流派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看起来很漂亮的理论与观点。人们只要在各自的理论框架下来讨论是非,就永远没有宁日,因为这些处在不同理论框架下的言论,都是“师其成心”的表现,亦即是没有丧失偏狭、固执之“我”的缘故。为解决这一问题,庄子提出“莫若以明”(即“不如用明”之意)的办法。笔者曾著文论证过,“以明”即“用明”11]。“用明”即“以道观之”、“以道视之”、“以道论之”。故“莫若以明”与“照之于天”,其意思是相同的,只是说法有所变化而已。
从语言的表面看,“莫若以明”与“照之于天”,都与视觉的“看”有关系,而与“天籁”——道之声无关。其实不然。天籁(道音)是通过声音的途径来揭示道,而“莫若以明”与“照之于天”,是通过视觉的途径来揭示道。老子早已经指出,通过人的感官方式来把握“道”,都有其困难性,故他说:“视之不见名日夷,听之不见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日微。…‘道之出口,淡乎其味”。因此,“莫若以明”仅仅是转换了论证的角度,即从视角的角度再次讨论“道”,而其所说的“看”,也并不是感官意义上用眼睛去看,仍然是抽象的理论思维,即从某一个理论视角、立场出发来思考问题,甚至还可以说是以理论性的想像去看问题,而不是看任何具体的事物。也即是说,从道的角度看,人类语言中“彼此”之分并不是固化的,每一个具体事物从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可以看作是彼或者是“是”(此)。生死在语言的框架里表述的是两件性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事情,但从生命本身的过程看,生的同时就蕴含着死的因素,而死的同时又蕴含着生的因素。虽然有时候,死与生已经不属于同~主体,如人从出生开始,就一步步地接近死亡,而人死亡之后,新的生命形态就从此死亡中产生。
所以,彼此、是非、生死都处在永无止境的过程之中,是不能做固化的理解,像语言中名词所表现的那样截然不同。这就是从道的角度看问题所得出的真理性认识,也是“用明”的结果。既然“莫若以明”即“照之于天”的结果如此,那么,我们人类各种有声语言斤斤计较、仔细分辨出来的是非对错,相对于“天籁”(道之声)的“大音希声”,或自然而然的一切声音而言,又与真理性的认识相差何啻万里呢?《齐物论》开头一大段从声音——人籁、地籁、天籁到抽象的“莫若以明”、“照之于天”论证角度的变化,给后来读者的理解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而这种不见痕迹的论证视角的变化,也与庄子以有法而无法的“卮言”言说方式密切相关。 二、“天籁’’与《庄子》中以“天”为词头 的词汇分析 除“天籁”之外,《庄子》文本中以“天”为词头的词汇还很多,天均、天府、天倪、天道、天运、天年、天放、天德、天乐、天伦、天门、天游、天极、天机、天性、天理、天壤、天韬,天帙、天地等,在这些词汇中,“天”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作为限定语,是指大自然的本有状态,此一层意思,实与“道”的意思相通。只有极少数词汇的“天”字不是这样的,如“天地”是两个名词联系在一起,“天”并非作为限定词来修饰“地”,而是以“天地”来代指实体性的大自然本身。“天运”即是指大自然本身的运动。“天年”一词中的“天”字虽作定语,修饰“年”,其词义是指自然而然的寿命极限,没有多少哲学意味。除此三个以天为词头的词汇之外,其他以“天”为词头的词汇就非常具有哲学意味了。
天道、天德、天极、天乐、天伦、天放、天游、天机、天性、天理这些词可以作为一组,但考虑到道、德、极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词汇,可以另作一组,而将天乐、天伦、天放、天游、天机、天性、天理另作一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