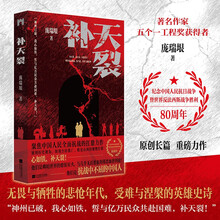第一章 劫后余生
那一夜,真长。除了两个女人,马家寨的好汉们厮杀半宿,终于筋疲力尽,在血泊中酣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东方开启了一线鱼肚白的天眼,似乎不忍见下界的凄惨,惊恐地眨了一下,又昏黑了,只留下天边一颗孤星,明明灭灭,凄凄迷迷,昏昏暗暗,惨不忍睹般照着马家寨残破的山门。
门洞大开,入口处,泥浆与肉浆混凝,铺出一条血路,又被马蹄戳得坑坑洼洼,一直通向门楼。城楼不宽,被横七竖八的尸体铺满,间或露出半块青石板,却被大雨冲洗得干干净净,只有石头缝里还有残血,血水浸染着杂草,一些淡红的细流慢慢往下洇染。
万籁俱寂,鸟不啼,虫不鸣,连风声也收敛了行迹,只有血腥味——浓郁的血腥味,如屠宰场一样熏人的气味,在破晓的清冽氤氲中弥漫,挥之不去,随着地气的上升令人眩晕,令人窒息,令人心悸……突然,一个孩子的哭声响起,打破了坟场般的寂静。那是婴儿的啼哭,开始如猫鸣,逐渐由微弱到强劲,拔高为尖利而悲怆的号叫:“哇,哇,哇——”哭声穿云破雾,响彻城楼,响彻山寨,声飘四野,既带来了生机,又加深了恐怖。
这天,是公元1259年(宋开庆元年,元宪宗九年)4月29日。
在死人堆中,马青苗醒来了,全身都被湿漉漉的血污包裹着,黏稠而腥臭,从头摸到脚,没有伤痕,只有下体绷裂似的疼痛。这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混沌中挣扎着坐起,她一甩头,听见了婴儿的哭声,震撼着女人天生的母性意识。顺着哭声摸去,撩起浸在血水中的裙子,捧起胯中肉团,一个小人儿在她手中挣扎。她恍惚了:孩子?我的?是啊,凤儿不是说我怀孩子了吗?不是说我要当妈妈了吗?想到这里,她呼喊起来:“凤儿——凤儿——”没人应答,只有城楼外一棵大树上的乌鸦被唤醒,哇的一声大叫,从她头上掠过,带起一丝风,激起她身上的鸡皮疙瘩。啊,怀孕的事一直瞒着父亲,怎能让他知道女儿当妈妈了?她赶紧把孩子往胸前抱。
搂近身边,她摸到婴儿的腿间,藕节一般的交接处,一个小小的肉蒂,她惊喜地喊出了声:“儿子?我有儿子了!”儿子了——儿子了——回应她的,是群山旷野的回音,拖声绵绵,空空荡荡。
“安节,你当父亲了……”她刚喊出口又噤声了,如果父亲知道孩子是谁的,他不把钓鱼城抄了才怪!可是,父亲虽然疼女儿,不是一直遗憾她不是男孩吗?我的肚子争气,这不给他生了一个?!虽隔一辈,也是血脉相承啊,他会高兴的。
“爹爹,你有小外孙了——”青苗的喊声压倒了孩子的啼哭声,终于唤醒了黎明,朦胧天光中,她看见四周躺着的都是尸体。
她忽然清醒了,想起半夜发生的事。
那时,她睡不着,正在床上翻来覆去,肚子越来越大,怎么掩饰?父亲发现怎么办?突然外面响起咚咚的敲门声,只有父亲敢这样来半夜敲门,不得了!她扯起被子盖住身子,对门外喊:“睡觉了,有话明天说!”是父亲,声音发抖:“青苗,敌人杀来了,快进山洞,千万别出来……”她不信,也不怕,翻身脸朝里,凤儿一把掀了被子:“你爸的话也不听?”“怕死你滚洞里去!”青苗又将被子扯过来,“谁要敢杀进来,老子做了他!”“马寨主从没这样惊慌过,情况一定紧急。”凤儿又劝小姐,“就是你能抵挡敌人,孩子怎么办?”“死了才好,免得挺个大肚子不敢见人!”丫鬟比主子懂事:“娃娃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安节将军的种!”青苗更生气了,翻身坐起道:“他个鬼东西,把累赘种给我了,他妈的倒快活!”“他哪晓得你怀孕了。”“他不晓得你晓得,你就知道让老子装病,叫你去找他,几个月都没找到,没用的奴才!”青苗边说边下了地。
拉开门,一道闪电劈来,炸雷跟着响起,门板摇晃了,跟着大雨倾盆,哗啦啦如天河决口。凤儿顶着大风关上门,推开橱子,拉手一抄,架起小姐两只胳膊,反背着她进了橱柜后的小门。
里面,过去是青苗母亲的佛堂,供桌上有她的牌位,下面是个地洞,洞里是山寨的珍藏。放好橱柜,关了洞门,连风雨声也听不见,两人累了,在一堆绫缎上躺倒。
父亲怎么总不来?青苗肚子渐渐疼了,推凤儿起来,要她出洞看看。青苗等得心里起火星了,凤儿还没回来,她火冒三丈,捂住肚子出了房间。风停了,雨止了,伸手不见五指,院子里漆黑一团,静得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她的心揪成一团,天天在肚子里踢打的孩子,莫非被吓着了,怎么一动不动?走出院子,心中一沉:城楼上没有一点亮光,火把、灯笼从来彻夜通明的,也被大雨浇灭了吗?即使都追赶敌人去了,也该留人把守啊,老头子糊涂了?!肚子疼痛加剧,她发起小姐脾气来:“人死光了吗?喘气的出来一个!”一片死寂,只有心跳如鼓。她慌了,顺着城堞摸过去,被人绊倒,跌在地上,孩子像在肚子里翻跟头,掏肝摘心地折腾,她疼得要打滚。强忍着疼痛摸去,是具尸体,没头,尸身胸脯没毛。她再往前爬,在冷冰冰的肉身上爬过,身上湿漉了,沾的是泥水还是鲜血?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冷,彻骨之寒,冻僵了四肢,冷得爬动的力量也没了。可是,要找父亲,她忘了恐惧,忘了疼痛……终于,摸到一把浓密的大胡子,是父亲的头!硬如岩石,还长在脖子上,她有了希望,喊叫着爸爸,伸手扶他,却见他身子下半截空的!只有一堆软绵绵、烂乎乎的东西。青苗毛发竖立,一股凉气从丹田上升,直冲天灵盖。她不敢哭,怕又一次昏过去,想把父亲的五脏六腑都装进腔子里去,可是肠子滑溜溜的,抓不住,装进去又滑出来……忙乱中,天渐渐亮了,终于看见死去的父亲:四方的腮帮子,显现出铁的棱角,兜腮胡子根根乍立,簇拥着大张的嘴,是继续喊着杀声,还是在呼唤唯一的女儿?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更可怕——眼球突出,眼白充血,是不是临死还想见青苗一面?他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女儿了,不是他不想见,是女儿不敢见他,是女儿不愿见他。这,都因为怀上了孩子啊!头脑仿佛炸开,腹部一阵绞痛:眼前金星四射。
“爸爸——”她发出撕心裂肺的一声大叫后,昏死过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