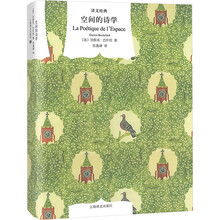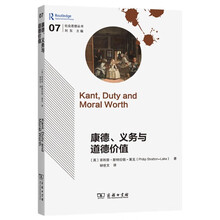第一章
首先,我想说,我不具有那样的天赋,凭借想象力和表现力,妙笔生花地为读者创造出这个人物——基里诺·西多诺维奇.拉祖莫夫。他按照俄罗斯的风俗,自称是伊西多尔的西里尔之子。
即便我曾以任何鲜活的形式拥有过那样的天赋,很久以前,它也在语词的荒原下窒息。众所周知,语词是现实的劲敌。多年来,我一直在教语言。这份职业,对常人本可秉承的想象力、观察力和洞察力,终会是致命威胁。教语言的人,必将迎来这个时刻:世界不过是由许多语词构成的地方;人似乎只是会说话的动物,并不比鹦鹉有趣。
因此,我不能凭借洞察力,观察或猜测拉祖莫夫先生的现实,更不能凭空想象出他的过去。即使要编造出他人生的大致轨迹,也非我力所能及。不过,我想,哪怕不用声明,读者们也能在书中找到文本证据的痕迹。的确,本书取材于一份文献。我所投入的只是我的俄语知识。要完成此处的任务,我的俄语绰绰有余。这份文献是一本笔记或日记,只不过与日记的实际形式不完全相符。比如,大部分内容不是一天天地写成,尽管所有条目都注明了日期,但有些时间跨度数月,篇幅长达几十页。日记开头部分是回忆,用叙事的方式追述了一件大约一年前发生的事。
在此,我必须先插一句。我在日内瓦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日内瓦有一个片区,住着许多俄侨,被称为“小俄罗斯”。当时,我在那里有相当广的人脉。但我承认,我摸不透俄罗斯人的性格。他们态度矛盾,结论武断,经常出现特例。当然,对于一个精通多门语言的学者来说,这些都不应是问题。但他们的行为中肯定有别的东西,有某种特殊性格,其微妙的差异超出了语言学者的学识。在一个教语言的人看来,他们最令人吃惊的,是对语词的狂热。他们收集语词,拥抱语词,但他们不会将语词藏在心里。相反,他们没日没夜地将语词倾倒出来,激情四溢,洋洋洒洒。有时,他们还用得十分贴切,如同训练有素的鹦鹉,难免让人疑窦暗生:他们是否明白自己说的话?他们狂热的话语中有一份慷慨,与通常的饶舌大相径庭。但他们的话语太不连贯,称不上雄辩……我扯远了,非常抱歉。
拉祖莫夫先生为什么要把日记留在身后?强作解人可能是白费心思。难以想象,他会希望有人看到。在此,许是人性中的神秘冲动在起作用。除了强行打开不朽之门的萨缪尔·佩皮斯,无数的人,无论是罪犯、圣徒、哲人、少女、政客,还是纯粹的白痴,留下自白性的日记,不仅出于虚荣,还出于其他谜一样的动机。语词肯定具有神奇的慰藉力量,因为如此多的人用语词来进行自我交流。作为一个性情平和的人,我接受这种观点:所有人真正追求的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宁静,或是某种宁静的独白。难怪,人们今日纷纷吵着要宁静。在写日记的过程中,基里诺·西多诺维奇·拉祖莫夫想找到怎样的宁静,我无法臆测。
无论如何,他写下了日记。
年轻的拉祖莫夫先生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他皮肤特别黝黑,这在来自俄罗斯中部的人身上不常见。他的五官若再精致一点儿,好长相就无可挑剔。他的脸就像严格按照蜡像的模样(接近古典的君子类型)铸成,但由于凑近了火堆,鲜明的轮廓消失在蜡液里。尽管美中不足,他还是相当英俊。他的风度也很好。在讨论中,他很容易被说理和权威所折服。与比他小的爱国者在一起时,他总是一副神秘聆听者的模样,会心地把话听完,再变换话题。
这类习惯,要么是由于智性不足,要么是由于不太自信,但却为拉祖莫夫先生博得了思想深刻的美名。他周围有许多夸夸其谈之徒,每日总是在热烈的讨论中搞得身心疲惫。在他们中间,一个比较沉默的人自然具有保留权力。基里诺·西多诺维奇·拉祖莫夫,这个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大三学生,在他的同学们眼中,是有骨气的人、可信赖的人。在很可能因言获罪——招来杀身之祸,有时甚至生不如死——的国度,这意味着他值得交心,值得分享违禁的言论。他性情温和,乐意默默为朋友效劳,哪怕牺牲个人之便也在所不辞,因此深受大家喜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