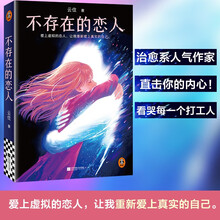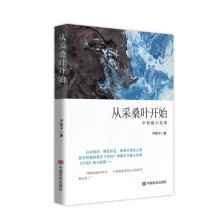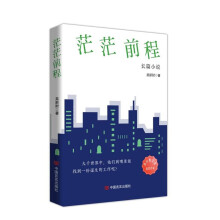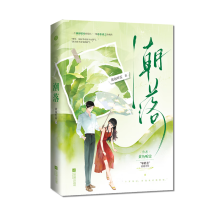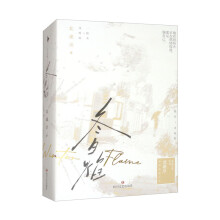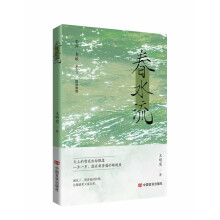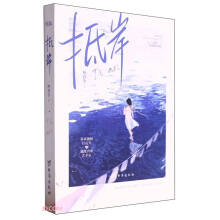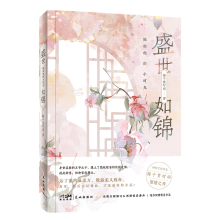葛云紫,女,1980年末生于安徽省蒙城县。一个不喜欢上学,却热爱读书的人。一个情商很高,智商很低的人。一个十三岁认为自己苍老而三十三岁还认为自己很年轻的人……作品以婚姻写实小说为主,透过夫妻矛盾,家庭矛盾,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矛盾,不只是反映矛盾,作者认为,将矛盾反映出来并没有意义,小说不能作为一种茶余饭后的无聊消遣,它是一个载体,是一个平台,它应该散发出一种正向的力量。所以,作者将佛陀所提倡的“看破”与“放下”老子所提倡的“无为”与“不争”,潜移默化在小说之中,表达了所求皆苦无欲则刚的人生态度,以小说的方式让读者感受和了知,索取、占有、控制、强迫是导致不安与痛苦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根源。只要践行了“看破”与“放下”,只要践行了“无为”与“不争”,所有的矛盾、纠葛、冲突、暴力都会自行消解,都会烟消云散,从而生活在一种恬淡平宁、安详和合之中。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