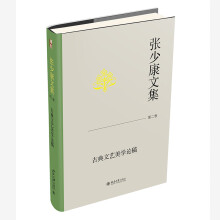一般社员却不是那样。上工集合的钟声,其实是挂在树杈上一根不长的铁轨,“铛”“铛”敲响,他们得等些时间才从家门出来。沿集合点的房根儿一蹲,或是一坐。把烟锅子掏出来,装上烟,点上火,“吧”、“吧”抿着嘴抽。等队长派完活,三三两两地分往各处。我们学生也这拨几个那拨几个跟着去。到了地头,先坐上很长一阵子。又“吧”、“吧”抿着嘴抽。一锅一锅地抽,也不说话。得抽上一个小时。带头的说:“干干吧!”于是起身干活。干不到一小时,领头的又喊:“歇会儿吧!”于是我们又集拢到一起,坐下。又“吧”、“吧”地再抽。他们不言不语,就是抽烟。最后领头地看看天,看看太阳,说:“到时候了吧!”就领着我们往回村的路上走。快到村子了,那铁轨准时地响起来了。他们压着钟点干活的本领真是够绝的。我那时就在想,并且到现在也还没太想明白。叫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后来又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要学的,要接受的,究竟是什么?贫下中农怎么会是这样呢?
在黄村时,黄村公社下来了一个议题。让我们讨论如何给地富子女定性?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属于哪个阶层?他们是地富一样的敌人,还是该属于人民?他们该叫什么?能叫他们社员吗?不叫社员叫什么呢?在村里的各种表籍名册里,他们的成分该怎么填?
所谓地富子女,是指1950年全国土改时,家庭被划为地富,但本人还不够岁数(也许是到18岁),未被划作地富分子的那些青少年。他们如今有的已十几、二十几岁了,已参加社里劳动。他们算什么,该怎么对待。这摆在村干部、村老乡面前了。“人民公社社员”,当时是一个带点荣誉的称号,只有人民,属于人民内部的才能享有。这样就不能把地富子女称作社员,因为他们头上总有一个挥之不去、擦抹不掉的阴影“地富”。就像我们很长时期仍把那些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称作“摘帽右派”一样。显然仍叫“地富子女”已经不妥当了,该有个正式定名了。这批人,人数不少。这是公社面临的一个理论而又很实际的问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