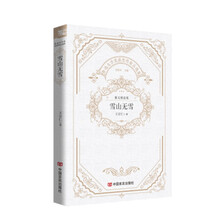我们几乎成了病毒本身
1885年7月6日,在法国阿尔萨斯,一头疯狗撞倒了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并对他连咬十四口。狂犬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因为医学界对狂犬病毒尚没有正确的认识。但这个名叫迈斯特的小男孩是幸运的,他被立刻送到巴斯德医生家中,巴斯德连续向迈斯特注射了十三次逐渐增强的稀释病毒,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秘密研制出来的狂犬疫苗,以此方法神奇地救活了小男孩。
巴斯德是最早认识并提取到狂犬病毒的微生物学家,为了证明研制疫苗的有效性,他甚至打算让一条疯狗先咬伤自己;但他也是幸运的,正当他要找疯狗来咬自己时,遇到了送上门来的迈斯特。他的治疗方式在当时尚属违法,一旦失败,后果难以想象。但巴斯德成功了,这一成功直接奠定了免疫学的诞生,是人类在治疗传染病方面的一次迅猛飞跃。
故事并没有结束,十年后,巴斯德死于急发症;又五十五年后,纳粹占领法国,当年的小男孩迈斯特已经是巴斯德研究所看门人。当德国士兵牵引着恶犬,病毒般占领巴斯德研究所并试图进入巴斯德墓地时,迈斯特在家中开枪自杀。
再后来,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生于捷克的赫鲁伯医生,一位在免疫学界和诗歌界都享有世界声誉的双料牛人,写下一首诗纪念这件事情,并感叹:“只有病毒经得起磨难。”
作为免疫学家,赫鲁伯无疑是最了解病毒的人;作为诗人,他无疑又最了解人性。一个这样的人说:“只有病毒经得起磨难”,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费解。但是,如果人有一天变成病毒本身,我就觉得好理解多了。
禽流感不是又来了吗?人们好像都很担心,不过我看并没有人真的在乎,谁也阻挡不住中国人骨子里的满不在乎爱谁谁。天气一好,公园里照例挤满了幸福和谐的人民,微博上到处是赞美空气、阳光和风景的照片,尽管这艳阳照得人空虚,春风吹得人伧俗,但没有人想过是否配得上这偶然的好天气。
其实,中国人早就“百毒不侵”,什么SARS,什么禽流感,什么水污染,什么毒牛奶、毒奶粉,什么滥用抗生素,不过浮云耳——中国人可能是人类历史近代以来最耐毒的一个种族。
我们几乎成了病毒本身,尽管我们不乐于承认。我们早就比病毒经得起磨难,只是当面对磨难或者病毒时,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作为一个人原本应该有的正常反应?
病毒可以杀死一个敏感的人,却对麻木的人无能为力。
你愿意做一个敏感的人,时有病痛时有伤怀时有愤怒时有不平,还是愿意做一个麻木的人,因为失去痛感神经可以经受任何磨难而不自觉,无欢亦无忧,不冷也不热地过活?
一个抽烟等车的人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只要我在等车,就会想起闵子骞路与山大北路交叉口,37路车站牌下,我曾经遇见的,一个和我一样等车的人。
他的头发虽已开始凋零,脊背也正在弯曲,可他的老婆很年轻,健壮,又有风韵。他的女儿也不大,小手臂还攥在他的手心里。他们一家人,和电线杆站在一起。我与他们隔着这根电线杆。
37路迟迟不来。“等车就是这样,三等不来,四等也不来。可是我有一个办法能让车快点来。”他突然对我说。
“现在你可以试着抽一支烟,你一抽烟,车就会来了。”
他掏出一支烟,我也掏出自己的烟。他给自己点火的时候,我的烟也已经点燃了。
我们一起从鼻孔里喷出第一口烟。
果然,37路车凶猛地跑来了,就像一个应验的咒语。
我扔掉香烟,跑上汽车。他的老婆和女儿也上去,只有他依然站在电线杆旁边。他朝车里摆摆手,怎么也不肯上。
“妈的,等车就是这样,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好不容易抽一支烟的时候,它反倒跑来了。这么好的一支烟,才抽了没一口,这不是祸害我吗?我就是不上。怎么着也得先将这支烟抽完再说。你们走吧,我等下一班。”
汽车凶猛地跑远了,电线杆下面只撇下他佝偻的身影。
这么多年过去,我还一直是等车上下班。几乎每次等车不来,我都会一边抽烟,一边想起他,一个有趣的抽烟者。
李小龙:作为神的三十五年
李小龙逝世三十五周年了,这三十五年发生了很多事,但和他有关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作为一个神,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不过,自从我知道李小龙以来,就对他甚少有好感。这可能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袒胸露肌、耍腿弄拳的人。看他的影片,总感觉他就是一个格斗动物,总是能把洋人打倒在地,还时不时发出阵阵怪叫。那动作我并不以为美观,那嚎叫我也并不以为悦耳。
在我的印象中,李小龙作为一个神,在中国人眼中和在中国以外的人眼中是很不一样的。李小龙用他的功夫征服了世界,成为一个不世出的武术大师而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龙迷”,而在中国人眼里,李小龙除了功夫之外,似乎又多了一重“民族英雄”的形象。他在电影里对洋人的拳打脚踢,和以此所赢得的全世界的声誉,都被当作这个英雄业绩的一部分,被人津津乐道。李小龙在那个时代的确满足了中国人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从这些画面的臆想中得到一些“复仇”的快感、满足甚至早已失落的尊严。即使到现在,这样一种附着在李小龙身上的情绪你也很难说已不存在。而这也正是我不喜欢他的一个潜在因素。尊严不应从这种暴力(即使是虚幻的暴力)中得到满足;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理解为另一种民族自尊心。
李小龙以一个武术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纪念,他的成功却很难说仅仅因为一身绝技。如果没有好莱坞在全世界的推销能力,很难想象会有现在的这个依然活着的李小龙。他难道不是众多好莱坞奇迹中的一个吗?难道不是西方话语权下的一个神话吗?如果没有西方世界对他的推崇,你能想象李小龙现在的面目吗?
他的被神化,更因为其离奇的死亡,以及他儿子近乎“父子同命”的悲惨结局,而变本加厉。越是扑朔迷离的结局,越容易成就这个神话本身,并让这神话更加弥久不衰。像庙里的菩萨一样,每年都能被不断地重塑金身、描眉画眼。不得不说,这阻碍了我对他好感,和进一步的认识。直到偶然读到林燕妮回忆成名之前李小龙的文章,才突然发现一个让我顿生认同和好感的李小龙。
林燕妮以李小龙“大嫂”的身份,以“耶稣在他的故乡永远是个木匠”的态度,回忆了年轻时代的李小龙。虽然文章中没有明确提醒,仍然可以看到,在美国长大的,这个叫做Bruce的年轻人,在其强大的身形后面其实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自卑和心病。文中提到,李小龙生理上的一个欠缺,是只有一个睾丸,他一度以为自己不会使女人怀孕;还提到他十几岁在香港做童星时,就被当时一个女明星诱夺童贞;以及他强烈的成名欲和孤独感,他说:“有时我会半夜醒来,坐在床上大哭一顿。”
我们虽然不能以此就想当然地认为李小龙之所以疯狂地迷恋功夫,并给人塑造一个“强大”的“硬汉”形象,是要弥补这些年轻时代的残伤,但是,能从一个亲近的人口中得到他另一面的真实,却能有助于消弭我心中李小龙强硬到有些乖戾甚至变态的想象。
相对于袒胸露肌、嗷嗷怪叫的李小龙,我更喜欢那个喜欢阅读尼采与海明威,失恋时写诗,独处时沉思的李小龙,我愿意为这样一个李小龙付出自己的好感。
“随着时间的流逝,英雄人物也和普通人一样会死去,会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而我们还活着。我们不得不去领悟自我,发现自我,表达自我。”这是李小龙曾经说过的话,很像一段伟大人物的临终遗言。如果全世界的龙迷,能够领悟这句话,那倒真算是没有白白崇拜李小龙一场。
以“病”为马
有一种病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一个人如果被一个罪犯长期绑架,最终会爱上罪犯,协助其犯罪;如果一群人被某个集团控制越久,尽管这个集团明明是在利用甚至迫害他们,他们仍会顺从和维护这个集团。
久病不仅能成医,病久了也会爱上病,舍不得它好,享受并且沉迷于那种痛。病人会在与疾病的痴缠中放任甚至放逐自己。他们巴不得医生能开一个“不治之症”的医学证明,这样就可以在疾病的掩护下,以“病”为马,为所欲为。
有这样一部电影,主人公因接受了某种抗抑郁症药物的临床试验,以测试它的副作用。当发现有测试者出现暴力倾向时,制药厂及时中止测试。但主人公却认为该药对自己很有效,谎称将药丢弃,暗中却继续服用。不久之后,他果然产生暴力倾向,并且人格也随之突变,原本温柔敦厚诚实善良的人,逐渐变得下流无耻,无恶不作。
当他决定将暗中服药的秘密告诉医生时,医生却告知他,他服用的药物和其他测试者不一样,只是普通的安慰剂,不可能有那些副作用。由此观众便明白,已经被证明的药物“副作用”成为他的一种心理暗示,那些下流无耻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在这种暗示下的对“副作用”的模仿。当心中的恶有了一个正当的外在借口时,他便没有办法不去作恶,并且爱上这种恶。
在济南发生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支援乡村医疗卫生建设,时兴医疗下乡驻点。有一位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前辈,为躲避下乡,谎称突患急病,瘫痪在床。那时组织对这类事情的检查很严格,并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掩人耳目,杜绝流言,该前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二十四小时不下床的“装病”策略。悲剧的是,正当全家人都认为风声已过,可以下床自由走动时,他竟然真的下不了床了,二十几岁的人从此便开始床上的余生。
还有个朋友,从大学毕业那天起,便拒绝找工作,抵触上班。他声称自己有家族遗传精神病史。上学期间除日常行踪较为诡秘之外,无人察觉他有任何异常。你不知道他是因为有家族病史才抵触上班,还是因为他要用长年不肯上班来证明其确有病史。
装病是病,装傻也是病。如果有人敢于证明自己是个傻瓜,他便可以像个傻瓜那样存在下去。但如果有人要让人相信他不是傻瓜,那就要费些力气。所以有病的人总是值得同情,没病的人总是活该。
在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你不得不常常和那些以“病”为马的人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当他们将借口、遁词、从别人处取得的宽容与谅解、客观环境的不追究不谴责以及“自欺欺人”等等盛装披挂在身的时候,你不得不为自己的“岂曰无衣”感到羞愧,就像桑丘面对疯狂的堂吉诃德,天真儿童遇见皇帝的新衣。
内省癖是一种无趣的病
中国是个讲究美德的国度,中国人有许多无用的美德。
比如中国人讲究“吾日三省吾身”,说你每天没事的时候都要反省一下自己啊,今天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了,什么话又说得不对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讲“反求诸己”,事情搞砸了,要多想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不能怪别人,怪就怪自己,要“引咎自责”,要“反躬自问”,要“闭门思过”,总之最后得出一个“都怪我都怪我”的结论就对了。
有人会说,如今哪还有这种“都怪我都怪我”的人啊,触目不都是那种“都怪你都怪你”型的?人人身上都长着芒刺,半句话不中听那刺儿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扎人,哪还有什么“三省吾身”、“反求诸己”,要真那样这个社会还用得着天天讲“和谐”么?
我得承认,如今的确是一个更崇尚“野蛮生长”的社会,用尽手段巧取豪夺,尽最大可能占有资源为己所用,先把自己喂饱喂大了再说,至于别人怎么着,有没有侵占别人的利益,有没有挤压别人的发展空间,那是没工夫去关心的。但我恰恰要说的是,正是因为有太多人内省成癖,自我收缩,才给了别人“野蛮生长”的机会。
理性的自省是一种主动防御,失去边界的自省不惟是被动,恐怕都有割地赔偿、卖国求荣的意思了。后者在职业生涯上来说,是乱了阵脚,而在个体的自我建构上,则变成了对自身价值的抹杀。那些职场上的失意人,生活中面容晦暗、委曲求全、隐忍不发的小人物,于是就越发地谨小慎微起来,将自我的边界无限收缩,谁都可以来踩几脚。
严厉的自省癖患者,往往把自己想象为圣徒,怀着赎罪与消业的使命,拷问内心,努力鞭打出自己皮袍下面的“小”来。这种道德的强迫症非但不会让人快乐,反而会使人压抑,无趣,难以接近。自省本身已经是一种很低的生活姿态了;越是低到尘埃里的人,往往越有一种自我完善的偏执,格局越小,越愿意精雕细琢,最终变成一件精致而无用的小摆件,去装饰别人的世界——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无趣的人生了吧。
自省作为人自我完善的必要步骤,一种修为,是没有错的,但自省也需要注意别踏入误区。
首先,自省要有边界。无边无际的自省是灾难,将事情不分外在环境和内在局限、大包大揽地自省和自责,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其他怀有善意的人们。
其次,自省不应放弃对外界的探索和占有。没有对外在的强烈好奇和赞美,再深刻的自省都是虚妄,都掩盖不住内心的荒芜。
最后,自省不过是一种反思和梳理的方法,切勿将方法变成目的。自省一旦成为目的,为自省而自省,那就是一种自恋,极有可能走向自我神圣化的不归路——中国有太多这种妄图“内圣外王”的怂包式妄想狂。
罗素有一个忠告: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也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便愈少,因为他若不能享受某一种快乐,还可享受另一种。我们都有内省癖的倾向,眼前无数有趣的事物不去欣赏,目光投向一无所有的内心;可是切勿以为,在内省癖的不快乐里有什么伟大之处。
青春是一种恶趣味
青春是充满嫉妒、猜疑、仇恨、尴尬和不堪的。青春是生命到达一个阶段之后各种痛苦矛盾的聚合裂变和大爆炸。
青春是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内分泌,弄不好就会失调:一次失调,贻误终生,就算后半生喝再多心灵鸡汤、打再多次金山夜话都弥补不回来。
它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是每个人都会生的一场病。
青春是有高下之分、有优劣之别的,青春是有阶级属性、有长短不同的,青春是有成败的,青春无悔的面具之下是别有幽愁暗恨生的。
青春是不公平的。每个人的青春若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终将会消失。要说公平,大概也只有这一点最公平。但在逝去之后,凡是值得回味的青春都是五彩斑斓、光彩夺目的;如果浑浑噩噩、毫无亮点,或者一念之差天堂入地狱的,那还要回味吗?恨不能一切归零,回炉再造,人生重启。所以到头来仍旧不公平。
所以青春并不值得珍惜,就算你再珍惜,失去之后还是会后悔莫及;青春也没有什么可挥霍的,就算你再挥霍,也不过是有限的力比多。青春并不太值得去过,那不过是一段时间而已,和少年中年老年的时间能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时空无限人生有尽,当我们看到天狼星时,已觉太阳渺小到无以复加,而在天狼星之上,又不知道有多么巨大的天体。人生如此短暂渺小,青春又有什么重要?
但青春仍旧是值得悔恨的,青春总是别人的好,自己的永远乏善可陈。青春的躁动,无非是因为生活在别处,因为太关注自我而又在肉体里将自我驱逐。无论是旅行、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还是恋爱、跳槽、出国、易容甚至变性,都不过是为了驱逐自我,接纳别人,以为从此功德圆满佛光普照;但当韶光逝去,还是这样地不满足,那样地有缺憾,既不爱自己,也得不到别人的爱。怎样硬塞进自己躯壳的东西,还要怎样再原原本本倾倒出来。而原本的自我呢?在爪哇国,在火星,还是就在自己身后却没有勇气反身去看?
所以我喜欢日本人对待青春的态度。看到樱花烂漫大好春光,万物勃发时代奋进,一切欣欣向荣,区区自己又何足道哉,何不在此年华一死了之?青春是一个瞬间的极致之美,而深植于日本人潜意识中“物哀”的审美观和生死观在此重合;青春期的自杀现象与其说是因为人生的苦闷,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乐趣。川端康成七十三岁时仍然选择自杀,并非因为对老去的绝望,而是对漫长青春的厌倦。
这个世界上最吊诡的事情恰恰在于,没有青春的人总在追忆青春,青春黯淡中年发福的人又企图虚构青春,为它涂脂抹粉、添油加醋,加上各种滤镜——这可怜的自恋和自卑,到底是如何支撑起他们空虚却又坚硬的躯壳的呢?
有人说怀念青春是一种恶趣味。我要说的是:青春本身就是一种恶趣味。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