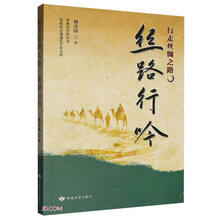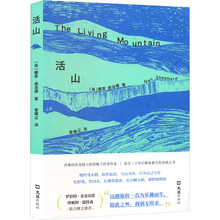博尔赫斯的夏天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我们当代文学心智的启发与影响是巨大的、无可回避的。若干年前,我们许多文学作品及文学写作者的大脑,真的成了博尔赫斯纵横驰骋的跑马场,直到今天,仍可以在我们的文学园地里听到博氏的马蹄嘚嘚,如影如风。我们随意打开一本文学书籍或杂志,特别是那种带有所谓纯文学色彩的杂志,许多作品中诸如图书馆、书籍、学者、某城、如梦如幻的战争或地震等等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意象反复出现,更不要说那种叙述方式与语境,与文学操作时的对古旧的历史陈迹的偏执狂式迷恋了。这里我们要说,博尔赫斯的诱惑确实是致命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完全丧失了自身所生存的现实土壤与精神内蕴的幼稚的文学,诱惑的同时更有了另一方面的作用,这便是对我们脆弱的自身的瓦解和践踏。
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租住在C市郊区一户农民家里,准备静心完成我构思已久的一篇小说,手头只带了很少的几本书,其中就有刚从朋友处借来的一本《博尔赫斯小说集》。对博氏及博氏小说的精神内核等有关背景材料,当时我实际上一点也不了解,这以前我只看过他极少的几个短篇,我也并不了解阿根廷以及整个拉美文化与欧美文化有什么具体的同和异。从这本小说集中,我直感到博氏本人从种族上或国别上讲是阿根廷的,但其精神体验却完全是欧美的,与阿根廷民族的现实内容应该并没有太多的关涉。我们一走进其小说世界,触目惊心的便是西方社会典型的人生与哲学命题,这便是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深切体验,以及时间与空间的直接体现形式:历史和文化的雄伟大厦及大厦倾颓以后抛掷一地的迷离碎片。在这里,我们确实沉落到完全丧失了时间与空间的迷宫之中,那么多的人或影,那么多的物与事、光与色,那么多棱的、圆的、交叉的图案和图景,似真似幻,似历史又似现实,迷迷蒙蒙地错落、搅和在一起,如夏天窗外的阵雨或山间的早雾一般,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明明灭灭变幻不已。你由着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动,不断地向前走,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方位始终是飘忽不定。你觉得你已走了好远好远,偶一回头,又会发现你似乎仍在原处。于是你不由对作为阅读者的自身也将信将疑起来。你已经不成为你了。
那个夏天已过去太久,手头又没有博氏的那本小说集来再一次重温,其中所描述的具体内容我真的早已淡忘,但是那种阅读的感受却仍是强烈的,记忆犹新的。那个夏天,我对计划要写的小说早失去起码的兴趣,而将自己整个深陷于博尔赫斯的世界。我面前的一切,现实中的一切似乎都呼啸着离我远去,让我时时在阅读的间歇如梦初醒,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我所租住的那样的房屋,我的房东那样的古旧的农民,还有头顶那样的太阳,那样的云彩,那样的白日和夜晚,全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古旧色彩,让我一眼看去只是异样不真实。特别是我所住的村庄紧靠C大学的后墙,后墙豁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供贪图方便的人出入。而这后墙偏偏又是由高一尺、长两尺许的古砖或仿古砖砌成,一律朱红色。我每天三次从这豁口经过,到学校食堂用餐,在夕阳晚照或寂静无人的中午,总有一股冰凉的东西从我浑身流过,我仿佛置身在某一座久远的废墟之上,仿佛沦落到幽幽的历史隧道的深处。特别是那个傍晚,我吃过饭出去散步,顺带把这本《博尔赫斯小说集》还给那位朋友。从我的住处到朋友家并不远,出了校门,顺一条宽阔却僻静的路面不平的街道走过去,踏上灯火辉煌、在C市极为有名的C大街,然后就可轻而易举地找到朋友的住处。这条街我走了多次,应该是轻车熟路,可是这天晚上我偏偏迷道了。我顺着那条僻静的街走了好久,却怎么也走不到朋友所住的C大街。我越走越急,越走越慌,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同样灯火辉煌的大街,但都不是我应该到达的那条。到后来我一身汗透,头微微发晕,神智有些不清醒。我知道我已走了太远的路,我应该到达的那条大街早已在无意中穿过,只是我自己没有发觉罢了。我应该调过头来往回走。就这时奇迹出现了,我一抬头,面前的一切竟异样地熟悉,我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的那条大街——C大街。当我敲开朋友的家门,在燥热的风扇前把自己的奇异经历讲给朋友听时,朋友思索良久,也无法做出让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又拿出一张很详细的C市街区图,越寻找我们越是一脸的惘然。后来我们若有所悟,同时默默地盯视着桌面所放的那本《博尔赫斯小说集》。看来我今夜所历竟是一篇很标准的博尔赫斯式的故事呢。
以后的许多时间,我一直在琢磨着想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小说,题目都拟好了,也是博尔赫斯式的,就叫《博尔赫斯小说读后随想》,却一直没有写成。也不是写它不出,是不愿费这个工夫。因为这种小说毕竟是博尔赫斯的,不是我的,我们的。
半边人
一九七七年正月十三一大早,我们一家人从安徽老家一个叫丁家罗庄的村子动身,分三路踏上了迁徙异乡的路程。第一路,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手上拎着几个简单的包袱,徒步十八华里到高河镇,然后坐通往安庆的公交车;第二路,我的表姐夫李以建和同村的一个兄长用板车拖着我们的全部家当,也是经高河直接送到安庆;第三路是父亲一人,他得辗转坐车到怀宁县治所在地的石牌镇,给我转共青团的组织关系。我们约好傍晚在安庆会面,然后从那里坐大轮去九江,去大山深处一个叫修水县汤桥公社的地方落户。
这是十分平常也平静的一天,天气很好,地面干燥,树林间或田野上弥散着若有若无的雾气。有几个得知消息的邻居站在路边为我们送行,其中一个长辈可能联想到什么,忽然间泪流满面。可是我们自己却感受不到半点离情别绪,相反,内心更多的是那种出远门的兴奋和激动。当时的交通不方便,公交车很少,我们在高河车站滞留了好久,傻呆呆地看站在木梯顶端的几个小矮人。这种小矮人在高河一带很有名,我从小就听过他们许许多多的故事。他们的脑袋是大人的,身子却像个小孩,永远长不高,并且代代相传,都在外面走江湖玩把戏。不过这天他们并不是在演出,他们可能也跟我们一样是来坐车的,或者正月里没事,吃过饭来车站闲逛。
此时此刻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平常而又平静的一天对我的一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次我们踏上的其实是一条真正的不归之路:自此以后将近三十年,我基本上还没有回去过一次,或者用另一句话来说,我每天都在返回,那是在梦中,在自己的潜意识里。自此以后我发现我的整个人基本上已给劈成了两半:一半在老家,另一半在异乡;一半是灵,一半是肉。每天都在挣扎,每天都在撕裂,每天都在用这一半去寻找另一半。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理解自己体验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和我有过相同的体验。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太脆弱了,对灵的要求太强烈了。反正我只是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彻底放逐之人、彻底遗弃之人,是一个对自己的另一半永远在寻求的人,一个时时刻刻处于灵魂出窍状态的人。我愿意以文字、以小说的方式,来很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对另一种存在的那种吁求。
二〇〇五年夏天,气温太高,写作状态不好,于是我利用这个时间,把《圣经》的《旧约》部分再完整地看了一遍。这个时候读跟年轻时读完全不同。年轻时喜欢在其中寻找一些微言大义,现在只想读一些平常的字句平常的故事。但正是这种阅读给人的震动更大。我忽然感觉那里面的一些人物,比如那个让人卖到埃及去的约瑟,在外地发达了,然后把他的父母家人全接了过去;还有那个路德,一家人流浪异地,结果男人们全在外面死了,只剩三个寡妇回来等等。这些怎么与我身边的那些流浪人、异乡人的故事如此相似?这些人,这些失魂落魄、祖祖辈辈在地面上荡来荡去的半边人,怎么也与我们如此相似呢?我感觉这绝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圣经》,这就是我们家里的一本家谱么。
说到这里,不知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我很想说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些可怜的半边人是永远不完整的,我们的另一半永远在那边,在天上。我真的很想以小说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另一半的永恒寻求。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