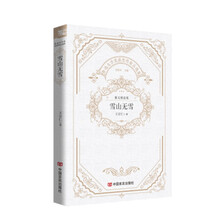鹤家乡有个很简单的童谣:“天上一只鹤,地上一只鹤,鹤天,鹤地,鹤,鹤,鹤——”小孩一听就记住了。
我们小的时候大人们白天忙于生计,儿歌多半是晚上暖被窝里跟孩子说的。这首儿歌是一个旁观者叙述的口吻,关于岁月的故事,淡淡口气,没有大的悲喜。
有些童谣少时听得快乐,老来听得释怀。这首十七字的童谣也如此。我现在念来,鹤影和鹤唳是那遥远处事物变淡的踪迹,从前旧芬芳。
我们方言里“鹤”字的发音很有趣,有很强的顿促感。鹤收拢翅膀的刹那,气流先在喉咙形成圆圆的一团,颚肌肉挤压收紧突然放开,气流分开,经鼻腔与喉间冲出——现有的拼音表达不出这样的发音。上回有朋友告诉我,台湾专门研究古语的学者,挖掘研究出一种古语符号能标注出吴音。可惜我一丁点儿都不知道。某些东西沉入时间的大海深处,成为我辈够不着的宝藏。
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说,老北京话“鹤”的发音是:hao(阳平)。
北京历史厚重,失去的也多。老北京“鹤”的发音,就像鹤已经飞远了,泣不成声那种。那里,惆怅的人抬头看流云。
“鹤”字在另外很多地方的发音带着去声,仿佛暗含鹤唳凄凉。而我们发这音时,唇形收拢成小圆,宛如熟透了的情人间挑逗的接吻,而声音很有游戏味道和幽兰清和味道。江南历来是人情温暖之地,擅长回旋之地。
在我们江南乡下,可以不问政治只问节气,鹤也跟卫懿公姬赤的亡国之事无关,它是山林之物,自然之物。这里鹤的发音,鹤好像就在人的头顶,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收拢翅膀降下来,让人看清它的眼神,和它瘦瘦脚杆上皮肤的角质层。
很多内心柔弱敏感的古文人称鹤为鹤友。当它细长的脖子弯下来时,漆黑闪亮的眼里满是垂向人心的询问:你,过得好吗?我不知道当年徽宗有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眼神,社稷高处不胜寒凉,他应该曾在他的喜爱和嗜好中寻找到忘记痛苦的力量,应该曾对这样的眼神有交流和领悟,譬如女人的眼神曾给他的那样。
宋徽宗的那幅《瑞鹤图》,且不去揣度是否是宫廷画师代劳,民间有传说他因梦见仙鹤与祥云绕宣和殿飞舞,也有传说某天真有此景,善绘花鸟的徽宗于是画成这个。意图是否在于宣扬皇室安稳天下太平?或是透露他更内向更隐秘的心事?我倒是比较倾向于悲观主义的隐喻:羽翼带它们到命运的轨迹去,皇朝和岁月,终将成为鹤一样扬长而去的背影。
有人认为若一个女人对外人强调二人间好合时,这二人间多半出了问题。这幅画倒也是看得出徽宗对朝廷世事的操心和苦衷,以及他内心的不同方向。
周邦彦作有“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帏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筝……”民间传是写徽宗与名妓李师师间的好事的,像现在所说:政治家的隐秘情事,可能会引起一场新闻风暴。不过旁史有载,徽宗在女人与书画之间还是有轻重之别的:金人劫掠宫妃宗室,徽宗未有异色,至搜取书画,始有喟叹——若此记载真当,那徽宗的境界也真当有意思。
作为一个人,他内心想要的丰盈,被皇朝皇位掠了去的那部分,要用他的艺术嗜好来填满。他时常一退朝便让自己埋没于纸墨金石间,仿佛编织和迂回在生命中的矛盾间,他要尽量让它们柔和好看一些。
世人有评:“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可是,你们看懂我了吗?感觉到我手指端的凉意了吗?知道我什么时候曾潸然泪下吗?他的绘画和诗句以及画面周遭的朱红印章,如今还在这么说。
金人人汴京时,徽宗耳边是否有鹤唳风声?我很想知道他当时耳中心中若有风鹤之声会是怎么样的。变数,劫难,峦徊,路转,也许如他后来在北地异乡心血所记:“……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我相信,他所依赖的那些嗜好,并没有能帮助他消除与这个世界之间的障碍感,也没有能说尽他内心的迷失。他本人亦如鹤影,徘徊于浑浊和清澈之间,留给我们一场唯美空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