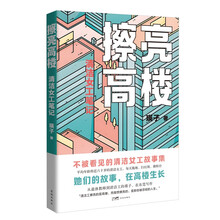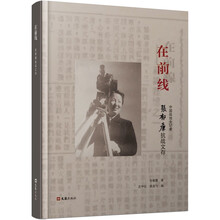《那年北漂》:
一些女同事听到这个选题吓了一跳,我倒没有什么阴影。我这个从小就立志做新闻记者的人,对于未知的人和事总有一种天生的好奇感,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选题,并很快联系了昌平殡仪馆前去采访。
采访之前,我查阅了许多信息资料,媒体对于殡葬业的报道多以负面居多,暴利、惊恐这样的字眼充斥眼球,殡葬这个神秘的行业在公众的心目中又多了一层阴影。而作为专栏记者,这些报道和资料只能作为参考,我需要打开我的视角走近殡葬工人,发现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昌平殡仪馆,馆领导首先带我参观他们的工作间,讲解操作流程。殡仪馆的工作间干净整洁,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阴森恐怖,偶尔传来一片哭声和哀乐,这才让人感觉到一丝悲凉。
最悲凉的是火化车间,殡仪馆领导特许我们进入火化车间拍摄。我看到了家属目送亲人最后一程的悲痛场面,第一次看见由人化为灰烬的悲凉场景,我凝视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引发了我关于“一生何求”的思考。
人的一生到底为了什么呢?不管荣华富贵,不管卑微贫贱,人的结局都一个样。富贵也好,贫贱也罢,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殡葬工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给人无限的神秘感。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采访了解殡葬工人的生活,殡仪馆领导推荐了他们单位的一对未婚夫妻作为采访对象,男的叫聂亮,女的叫汪婷。
聂亮和汪婷都是80后,东北人,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一起来到昌平殡仪馆工作,并很快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聂亮高大帅气,从事遗体整容工作,汪婷端庄秀美,足有一米七的个头,从事葬礼主持工作。
我和很多人一样,不理解两位仪表堂堂的年轻人为什么选择了殡葬服务工作。汪婷告诉我,她第一次见到遗体之后,当天晚上就不敢睡觉,不敢关灯,心里的阴影挥之不去。聂亮从事遗体整容工作,经常遇到高度腐烂的遗体,那种恐惧感更是不言而喻。
聂亮和汪婷在昌平殡仪馆工作了三年,对逝者的恐惧感早已淡去,但是来自生者的不理解又让他们感受到另一种恐惧。
“最开始我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家里人就强烈反对,我姑姑就说,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干这个工作。”汪婷说话的时候很淡然,殊不知她的背后却遭遇了各种冷遇和尴尬。
在常人的眼里,与殡葬如影随形的词语包括死亡、尸体、恐怖,殡葬工人很难融入周围的社会。他们很少有朋友,逢年过节很少走亲串门,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握手、吃饭、聚会,他们总是生活在狭小的自我世界里。
“是什么让你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呢?”我问汪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从事着正当的社会职业,我也有自己的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的梦想很简单,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北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和自己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汪婷的脸上露出自然的微笑,她告诉我,她和聂亮从大学开始恋爱,整整五个年头了,他们凑足首付款在昌平买了房子,并且计划在年底步入婚姻的殿堂。
“我每天主持葬礼,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亲自主持自己的婚礼,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汪婷性格开朗,说到婚礼她格外兴奋。听她这么一说,我一下子肃然起敬,因为自信,因为执着,此刻汪婷在我的面前显得如此美丽。
“这个创意不错,还有别的创意吗?”作为未婚青年,我很乐意倾听她对于婚礼的各种想法。
“我们的婚车希望是黄包车,他驮着我过去,我不希望坐什么加长的林肯,坐一个小时林肯,不如一辈子安安心心坐黄包车。”汪婷说完之后,我看了看坐在一旁的聂亮。聂亮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是他的话不多,他一脸憨厚地说:“婷婷的浪漫情怀多一点,这事由她做主,反正我都听她的。”说着说着,我也被感动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采访结束后,我主动和汪婷、聂亮握手,并且对他们说:举办婚礼之前通知我,我一定向你们道喜。
参加一对殡葬工人的婚礼,这是常人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这个社会对殡葬工人有着太多的误解和偏见,而我主动打破这些禁忌,因为我被汪婷和聂亮的执着深深打动,被他们的幸福深深感动。
幸福是什么?从古人造字的角度来看,福者,一人一口一田,各自修行于业田,衣食无忧即为福。古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如此简单,而今的许多人物质生活早已衣食无忧,却永远感知不到幸福的真谛。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主观感受,没有客观标准,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命题。聂亮和汪婷被社会边缘化,不被常人所理解,然而他们的生活一定有着别样的幸福。他们的幸福是对事业的执着,是对爱情的忠贞,他们的幸福感由心而生,由内而外,按照我的自定义来说,他们可谓是幸福的样板。
当天晚上,我把今天的采访故事说给馨儿听,她同样被聂亮和汪婷的故事深深感动。
“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幸福,在北京也会有自己热爱的工作,也会有属于我们的家。”馨儿向我表达了她的意见。
我点了点头。
“我们要是办婚礼,你就开着坦克来接我,因为你是坦克手贝塔。”馨儿一边说一边大笑。
“好!反正我也都听你的……”我和馨儿有说有笑,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