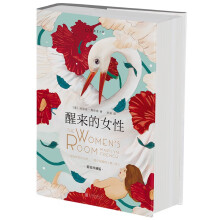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到我的卧室里来,”我说,“那里有面镜子。”
我打开屋门,点上了蜡烛。罗西跟在我后面走了进来,我把镜子举起来一些,这样她就方便看到自己了。在她整理头发的时候,我看着她镜中的形象。她拿下两三个发卡,衔在嘴上,拿起我的一把梳子,把头发从后面往上梳。完了把头发盘在头顶,轻轻地拍了拍,接着又把发卡别了上去;在这样梳着的当儿,她看到了镜中的我,冲着我笑了。在插上最后一个发卡后,她转过身子脸朝着我,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平静地看着我,蓝色的眸子里依然是那种友好的笑意。我放下了蜡烛。屋子很小,梳妆台就在床边。她抬起手来,轻轻地抚着我的脸颊。
现在,我真希望自己如果没有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这部书就好了。要是你能把自己写得和蔼可亲、生动感人,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也未尝不可。这一手法在表现伤感的幽默和朴素的英雄气概上,更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你看到读者的眼睫毛上闪着晶莹的泪花,他的唇边浮着会意的笑容时,你会为你用第一人称写出自己,感到由衷自豪;但是如果你不得不把自己写成个十足的傻瓜时,这一手法就不可取了。
不久之前,我在《旗帜晚报》上读到过伊夫林·沃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用第一人称单数的手法写作小说是一种令人鄙视的做法。我希望他能解释一下他之所以这么认为的原因,可他就像欧几里得提出他著名的平行直线的论断一样,只是抱着信不信由你的那种随意态度,说出了他的看法。我心里更觉得疑惑了,于是,我问了阿尔罗伊·基尔(他博览群书,甚至请他写序的那些书他也要一一读过),让他给我推荐一些有关如何写作小说的书籍。遵照他的建议,我读了珀西·卢伯克写的《小说技巧》,从这里我知道了写作小说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亨利·詹姆斯的写法。在这之后,我又读了爱·摩·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了解到写小说的唯一方法是学习爱·摩·福斯特本人的写法。后来,我又读了埃德温·缪尔的《小说结构》,从他这里我什么也没有学到。在上面提到的各本书里,我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原因,知道一些小说家——比如说笛福、斯特恩、萨克雷、狄更斯、艾米莉·勃朗特和普鲁斯特这些曾经很著名现在无疑已被人们遗忘的小说家——为什么要使用伊夫林·沃所鄙视的这一写法。随着年事的增长,我们越发意识到人类的复杂性,其不通情理和前后的矛盾性;为此,一些本该转而去写严肃题材的中年或是老年作家,结果却让自己沉迷于写虚构出的人物的一些琐事。因为如果你研究的对象是人的话,很显然,让你自己去关注小说中的那些前后一致、扎实丰满和富于意义的人物形象,远比去关注现实生活中那些非理性的揣摩不透的人物,要理智得多。有时候,小说家觉得自己像上帝一样,准备把他的人物们的一切事情都讲给你听;可有的时候,他却不是这样;这时,他不告诉你有关他们的一切,而是把他自己的那点儿事情告诉你;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越来越不像上帝了,所以,当我听说随着年事的增长,小说家们越来越不想要描述在他们经验之外的事情时,我并不感到奇怪。第一人称单数的写法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这一具有局限性的目标。
罗西抬起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这一点儿也不像在那种场合下我想要自己表现出的样子。从我哽塞的嗓子眼里,我发出一声呜咽,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的羞怯和孤独(不是环境上的孤独,因为我一整天在医院里就是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是精神上的),还是因为我的欲望太强烈了,我开始哭了起来。我真为自己感到羞愧;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却也是枉然;泪水从我的眼眶里涌了出来,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罗西解开了她的胸衣,摁低我的头,直到我的头伏在了她的胸口上。她摩挲着我的脸。
像她臂弯里的一个孩子那样,她摇晃着我。我亲吻着她的乳房和她白皙修长的脖颈;她的身体从她的胸衣、裙子和衬裙中间滑落出来,有一会儿我搂着她穿着紧身褡的腰部;临了,她屏住呼吸,缩紧身子,解开了紧身褡,只穿着汗衫站在了我面前。我用手抱着她身体的两侧,能感觉到紧身褡在她白嫩的皮肤上留下的压纹。
“吹灭蜡烛。”她说。
当晨曦透过窗帘窥了进来、驱赶走滞留的夜色、显现出了床和衣橱的形状时,是她唤醒了我。她吻着我的嘴唇,披散下来的头发拂在我的脸上,痒痒的,就这样,我醒了。
“我必须起来了,”她说,“我不想让你的房东看见我。”
“时间还早着呢。”
在她向我俯下身子的时候,她的乳房就沉甸甸压在我的胸脯上。不一会儿,她下了床。我点燃了蜡烛。她对着镜子,扎好了头发。有一会儿,她看着自己的玉体。她的腰生来就细,所以,尽管她的身体很丰满,却依然十分窈窕;她的乳房很坚挺,它们直直地耸在胸前,就像是雕刻在大理石上的美人。这是一个为爱的欢悦而造就的身体。在摇曳的烛光下(此时,晨曦已经快要盖过了暗淡的烛光),她的整个身体都呈现出银光闪闪的金色,只有她的坚挺的乳头是淡红色的。
我们默默地穿好衣服。她没有再穿紧身褡,而是将它卷了起来,随后我用一张报纸给她包好。我们踮着脚尖穿过过道,在我打开房门、我们要步到街上时,晨光扑面而来,就像一只小猫顺着台阶一跃而起。广场上还阒无一人,阳光已经照耀在了朝东的窗户上。我觉得自己就像这黎明一样的年轻和充满活力。我们手挽着手走着,一直走到了林帕斯路街口。
“就送我到这里吧,”罗西说,“万一碰上什么人。”
我吻了她,望着她走远。她走得并不快,身子挺得很直,是一位乡下女人的那种坚实的脚步,喜欢感觉到她脚下肥沃的泥土。我回去也不可能再入睡。于是,我信步走着,一直走到了泰晤士河的堤堰。河水映着旭日,闪烁着明亮的光点。一条褐色的驳船正穿过沃霍尔大桥的桥洞,一只小船上的两个人正贴着河沿奋力地划桨。我突然觉到自己饿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