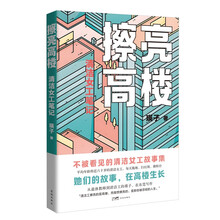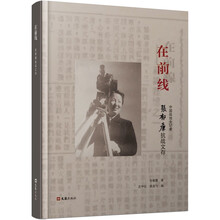《流远 我的水利人生》:
我于1962年从湖南省安化县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为武汉大学)。按照当时的学制,本应于1967年7月毕业并分配工作,可却一直推迟到1968年9月才正式分配工作。我们在大学校园里整整待了六年时光,好不容易才等来了毕业分配这一天。当时,摆在同学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选择分配志愿。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大学生都成了“处理品”,没有现成的工作岗位供我们挑选。等待我们的是去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或者到农村插队落户。我们这个年级和专业可以去的省份只有七个:即湖北、江苏、江西、广西、山东、黑龙江和甘肃。其中除了江苏、江西和广西是安排去农村插队之外,其余四省都是去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我当时曾经同我们班上两位最要好的男同学商量,准备一块去甘肃。可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却改变了那两位同学的分配去向。
一天下午,我们三人一块去离学校不远的武汉市洪山公园游玩,算是对我们曾经在那里度过了六年人生中最宝贵时光的武汉市这座花园般的历史名城的最后一次告别。当我们刚刚来到公园中离施洋烈士的大理石雕像不远处的一条林荫大道旁边的水泥长凳上坐下时,突然,两名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知识青年连忙向我们走来,并递给了我们两份小报。其中一名女知青连忙自我介绍说:“我们都是刚回城的支边青年。我是刚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回来的,她是刚从甘肃省农建师回来的。我们要求武汉市革委会重新恢复我们的武汉城市户口,并安排我们的工作。” 原来,她俩都是要求回城的支边青年。当时武汉市正在刮起一股支边青年要求回城之风,这两份小报就是这些支边青年自己编写并印刷出版的,实际上是向社会散发的传单,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我见她俩都是刚从大西北返回武汉市的,便对她俩说:“既然你俩都是刚从大西北回来的,能不能请你俩向我们介绍一下大西北、特别是甘肃的情况?” 她俩见我们有意打听大西北的情况,总算找到了知音,于是便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了她们在大西北的种种不幸遭遇,其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那位刚从甘肃农建师回来的女知青连忙对我们说:“甘肃那地方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不仅风沙大,而且干燥得要命,用水也很不方便。我们在那里待了将近两年,不仅从来没有洗过澡,也很少洗过脸。因为洗脸用的水要到很远的地方才能取来,而且是浑浊得要命的泥巴水。我们做饭时必须先将这些浑水放到脸盆里等上大半天,将泥巴沉到盆底以后,再将上面比较清洁的水拿来做饭。由于水的碱性太大,我们刚去时喝这样的水都不适应,大家都感到肚子痛,吃药也不管用。但也没有办法,每天都得喝这样的水,不喝就得把你渴死。由于长期不洗澡,有时候连脸都洗不成,我们浑身上下,包括头发都长了虱子。由于空气太干燥,刚到那里时,我们的嘴唇都裂了口,还经常出血,脸上也都布满了裂纹。还有,我们住的都是地窝子,周围又没有厕所.解羊只得到很沅的野抑早去锯.晚卜击己桌可不方便。有一天半夜,我和另一名女知青一块到外面解手时,突然发现很远的地方有一对蓝色的光点,好像是有人在向我们打手电。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是狼的眼睛,因为当地狼特别多。当时吓得我们俩跑回来了……” “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真话?”另一位同学连忙插话说。
“我要是骗你们我不是人。”她用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向我们发誓说。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跑到甘肃去呢?”我连忙发问说。
“唉,学校动员我们去支边,我当时已经十七岁了,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只好跟着班里的其他几位同学一块去了甘肃,谁知道到了那么一个死地方!” 她俩的一席谈话在我们的脑海中曾布下了重重的乌云。那两位同学因此改变了去甘肃的念头,选择了其他省份。而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仍然死心塌地地选择了甘肃。
在那个革命热情十分高涨的年代里,同学们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都有一个固定的程式:第一志愿是“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志愿才是你真想去的地方。而我却打破了这一程式,第一志愿就是“甘肃”,第二志愿才是‘‘服从组织分配”。由于这一特殊举动,我自然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了甘肃,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零三个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