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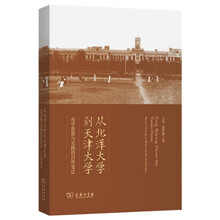




亲历者讲亲历事,众多一手资料,文献价值丰富。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进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改革,同时也开启了科技改革与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冲破旧的框框,调动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思想、体制创新、制度建设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作者全程经历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年代。结合自身学习、工作的实际,记录了亲历中国科教改革的心路历程。相信无数改革者的个人记忆,就是一部鲜活的改革开放史。
科学学的“四君子”
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许多活动中,人们经常会讲起上海的“四君子”。这是指全国人大原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冯之浚,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欧管理学院原执行院长刘吉,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夏禹龙以及张念椿教授四个人。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的合作,曾经活跃在科技界,并产生较大影响。
我曾见证了他们的合作,也略为了解后来他们分开的情况。1979年初夏,我所在的华中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举办全国科学技术史讨论会,他们四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自武汉顺流而下的长江轮上,四位中年同志顾不得眺望浩瀚的江流和两岸的风光,而在客舱里进行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他们从会上的初交到思维的共振,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就在这种激发状况下,边议边写,完成了第一篇合作的论文。”他们四人合作虽带有偶然性,但也有内在的缘由。他们都有工程技术专业的背景:夏禹龙曾在圣约翰大学学土木工程;刘吉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冯之浚就读于上海铁道学院铁道工程专业;张念椿则在同济大学攻读路桥专业。他们都有比较广泛的兴趣,均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栖”性。另外,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都有一段坎坷的遭遇。他们的合作体现了信息共享,思维共振,三维共构,情绪共染。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几年中,他们的学术合作小组,就是后来的所谓“工作室”,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文章。他们当中各有优势,夏禹龙理论功底厚,冯之浚擅长总结和口才,刘吉思想火花多,张念椿文字见长。他们合著的《领导科学基础》,一版再版,几乎成了全国轮训干部的教科书。他们还把视角放在战略研究上,1982年就上书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提出《关于建立和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刍议》,一篇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不仅刊登在级别最高的《中国社会科学》上,而且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重视。另外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周克,这位曾在“一二·九”中投身抗战的革命老同志,在解放军渡江前夕,领导了著名的上海江湾机场军火库爆炸,“长沿号”军舰起义,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首任上海市轻工业局长、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因实事求是地在党的会议上给当时炙手可热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了意见,在“反右运动”后期“补课阶段”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蒙冤21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8年才获平反。复出后他先后出任上海市科委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周克同志是一位非常开明、有前瞻的领导。他和他们四人首先组建了全国最早的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周克任首任所长。在周克同志的推荐下,夏禹龙后来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冯之浚进上海民盟当领导,直到民盟中央副主席;刘吉先后在上海市科协、上海市体改委、市委宣传部任职,后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为他们日后的发展建立了很好的平台。
夏禹龙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地下党员,现在应该近90岁高龄了。在科学学初创时期,他已经满头白发,但却是童子心。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在昆明召开科技政策座谈会上,会议人不多,会议之余正好看女排比赛实况转播。他的情绪随着赛况波动,和年青球迷的表现一个样,随童大林来参会的邓楠看到这种情况,总是哈哈大笑。有一年,赵红洲、蒋国华从北京到上海出差,曾到夏禹龙家里去看望他,老夏正在看球赛,回头呵了一声,又继续津津有味地看球了,好像没有这回事。夏禹龙长得酷似原国家科委主任、中宣部秘书长童大林,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吃饭,我也在座。人民日报一位资深记者错把老夏看成童大林,连忙整了整头发,毕恭毕敬地弯身问:“大林同志好。”老夏回头一句:“我不是童大林”。总之,老夏是位心态极好的人。老夏的理论功底好,他后来由于担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公务繁忙,学会的活动参加少了,但却在致力于研究社会科学学。
冯之浚从20世纪80年代进京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有20多年了。他还是全国人大的五届常委,可以说是资深常委。他参政议政能力极强,又善言辞,我在武汉一次陪钱伟长先生视察时,他亲口对我说,“民盟准备推荐冯之浚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但事情往往很复杂,加上他心脏出过两次问题,终于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干了很多年。我们相识三十年,他善解人意,有几件事我是难以忘怀的。1986年年底,我在华工党委选举换届中落选,他知道我心情不好,邀我上北京,并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为我订了一个套间。我在那里住了半个月,竟然写了一本普及高技术的小册子。不久又安排我们夫妇去上海过春节,同时也把当时在天津处境不好的何钟秀一家也请来了。我们两家在上海过年,也其乐融融。我在广州番禺建成一个大学时,他将学会的年会安排在我工作的地方召开,也算对我工作的支持。2001年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又推荐我到学会主持日常工作。我对学会也有感情,推掉了几个到民办学院当院长的机会,在学会一干就10年,得到了学会上下的认可。冯之浚是继钱三强、龚育之之后,担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第三任理事长。他在任期内,大力培养年轻人,广泛开展课题研究,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研究中,走在前面,把学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刘吉才华横溢,清华大学毕业后分在上海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就提升为工程师。在科学学学会里,被认为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经常会冒出闪光点。他先后担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市体改委副主任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政务繁忙,和科学学学术界较少来往。后来人们也知道,他大概要担负领导交办的一些事情。即使后来他到北京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时,也很少有人去找他,都体谅他的处境。我因为工作有时去香港的一些大学,偶尔也能在境外的一些报纸杂志上看到对刘吉的报道,说他是中央领导的智囊,云云。我和刘吉常有联系,虽然见面不多,但常常通通电话。逢年过节,他也会通过手机发发短信问候。前几年,正好我们都在北京,他请我吃饭,长谈了两个多小时。多年没有这样交谈了,我感到他的谈话很有深度,包括对“三个代表”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退下后,主要在上海中欧管理学院主持工作,也很忙。现在据说退了,但也担任该院基金会的理事长。这两年我们也在北京见过面,他还是一幅忧国忧民的样子。
张念椿原来和冯之浚都是上海铁道学院自然辩证法的教师。他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精明男人,但他在这个集体里,位置摆得很好,主要是做操作层面的工作。他忍耐性也很强,曾经伺候过生病多年的前妻。后来他也曾经试过下海经商,但不是很适应,听说他现在身体不好,很少露面。
真是应了古人的一句话: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们由于后来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也不在一个城市。他们中有的人也存在芥蒂。还是十年前,我有一次到上海开会,专门找夏禹龙谈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比较超脱,但他也认为,有些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我和他们几个人都很好,但有一点我可以证明,他们从没有在我面前攻击过对方,总的来说还是君子风度。
但是,他们的合作,取得过丰富的成果,在学会里面,一度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