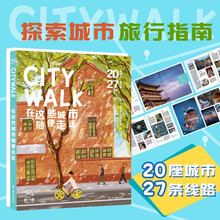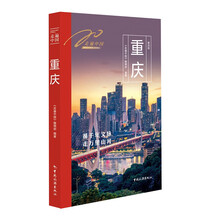《跟着本书游天下:烟花三月下扬州》:
1982年春天,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题目是《桥与引渡者》。祖父因肠道疾病恶化,自知停留于世的时间不会太久,于是提出到檀树湾看一座桥。
那不是家乡的桥。我的现居乡村已经没有一座木桥或土桥。坚固的钢筋水泥和由机器开掘出来的巨大石条足够架设大大小小的桥梁,并且都有崭新的命名。一座桥的诞生,不仅仅是一项工程的竣工,还为那部地方志增添了新的条目。我的同乡好友在电话里告诉我,回家的三道河上都修了钢筋水泥桥。祖父说,檀树湾的檀木桥是他亲手造的,檀木疙瘩里兴许还留着他的汗水。
我写信给祖父,赶完论文马上回去,去陪他看那座桥。然而,等我回来时,祖父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不能说话,但他的手势告诉我,他看过那座桥了,是在两个月前。
我伫立在夏天里的那座木桥头,在遥远的意念里,或是在切近的守望中,思考我的来龙去脉。我们家三代单传,我的父亲就是从檀树湾过继来的。
湾子四围的景色都向一座桥聚拢而来,包括那些优美而虚幻的民间传说,那些隐隐约约的前尘影事。我于一个露珠晶莹的早晨,借着一截牧童的牛绳来延续日渐淡漠的记忆,试图把它复制在我熟稔然而却陌生的那个小小山村。
也许我那远方的宗家门前曾有过这道木桥,也许儿时随祖父越过漫水河,跋涉到一个狭长的山冲里,见过这样的一座木桥。桥身由整棵大树的树干搭成,上面可能完全由行人的脚步踏平,光洁如镜,呈现褐红色的肉质的感觉。至于那个夏天我去那里的具体动因,当时的确莫可名状,现在也记不起了,能记住的是这座木桥酣睡的姿势以及它默默背负的耐力。
“真是一座好桥!”仿佛听到祖父这一声赞叹。他是说过,别人走他的阳关道,他却喜欢走这样的独木桥。
彼时,水稻们齐刷刷地俯下了它们谦虚的头颅。我还记得,那个宗亲家门前有好几棵高大的黄檀木,它们成了整个村子的威望,因而那个村子便被命名为檀树湾。
很远了。我是说时间。
那样的一棵檀树留在村子里,甘愿做桥;那样的一座独木桥架在河流上,衍生传说和故事。由人们的目光摩挲出来的所谓艺术品总是在外面流浪,哪怕它精致得像卢沟桥上的狮子。
我的论文参照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而行文迈开的第一步似乎是从这座老檀木的村桥起始的。我试着解悟一座桥,觉得它不只是把已经形成的河岸连接起来,不仅仅是为了沟通和畅达,而是存在于时间之上的一种再现,是对水流的动态个性和河岸静止状态的一种解构。在桥的横越中,河岸才作为河岸出现。河岸也并非作为坚固陆地的无关紧要的边界线而沿着河流伸展。桥与河岸一道,总是把一种又一种广阔的后方河岸风景带向河流,它使河流、河岸和陆地进入相互的近邻关系中——一如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桥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它因此伴送河流穿越河谷……始终而且各不相同地,它来回伴送着或缓或急的人们的脚步,使得他们能够到达对岸,并且最后作为短暂者到达对岸。桥以其独有的呈示方式把上天、大地、神佛和人类聚集于自身,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既是一个站立的人,也是一座躺倒的桥,或者是一段记忆与传说。甚或,我们见过的任何一个村庄,都是大地上的桥梁。
写到“引渡者”,我的脑子里总是不停地晃动着祖父的形象。我在想,我们的一切念头都曾经做过桥梁,虽然我们毕竟不是都能成为引渡者,祖父也不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