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我都会给七岁的女儿搭配好衣服,等她洗漱完毕,再给她梳个漂亮的发型。每天晚上,我挤在她的床上,给她讲睡前故事,跟她聊心事聊秘密,给她晚安吻,看她进入梦乡。我们说这是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事儿,我们说这是妈妈专属的特权。我每天按时下班,我尽量不出差,我想给我的小女孩我能给的所有陪伴。只是,我从来不敢想,若是有天我不在了,她会怎么样?
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大家都会心大笑。原来明星们也会这么笨拙,谁家里又没有这么一个笨手笨脚的爸爸呢?他分不清盐和糖,他找不到女儿的袜子,他可以在夏天给孩子穿上棉衣。那些妈妈看来自然而然的事情,到了爸爸手里就比登天还难。笑着笑着,眼里就会有泪,若是有天我不在了,爸爸会怎么样?
所以看到《亲爱的小孩,原谅我不能陪你长大》这本书的介绍时,顿时就被吸引了。安琪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世,安琪有八个孩子和一个不问家事的丈夫。面对死亡,安琪有那么多那么多放不下的事。可她没有悲伤,也没有放弃。她每天努力地教自己的丈夫,教会他做那些该为孩子们做的事,然后她才安心地笑着走完余下的人生。
安琪的丈夫和孩子们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在安琪离开后,米尔抚养孩子们健康成长,他们继续快乐地生活。我想,这也是每个妈妈都有的期望。这也是书名里没有说完的话:亲爱的小孩,原谅我不能陪你长大,但我不在的日子,你也要快乐。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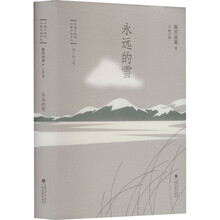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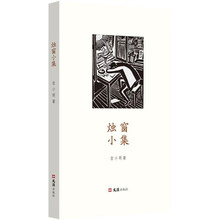

——《卫报》
★安吉一家是不幸的一家,命运对她们实在太过苛刻;安吉一家又是幸福的一家,因为爱,因为乐观,纵使阴云密布,却仍在缝隙里投射出积极之光。
——《每日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