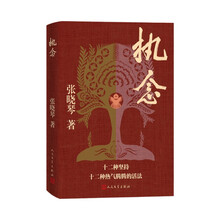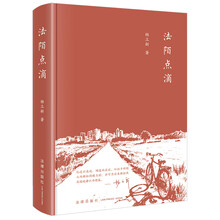荒谬与自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过下去,就是在回答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其余问题,诸如世界是否有三个维度,精神是否分为九或十二个范畴,都在其次,这些不过是游戏。人必须首先回答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真如尼采所言,一个哲学家必须以身作则,才能赢得尊敬,你就能领会这答复的重要性了,因为回答引领着决定性的行动。心灵易于察觉到这个事实,但理智若要明晰这一点,则仍需深入讨论。
倘使要问,依据什么来认定这个问题比那个更紧要呢?我会回答,根据它将会引发的行动来判断。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而死。伽利略掌握着至为重要的科学真理,然而一旦真理危及生命,他便弃之如敝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做得对。这一真理不值得赌上性命。
太阳围绕地球转,抑或地球围绕太阳转,其实这无关宏旨。说真的,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另一方面,我知道一些人为了赋予人生意义的理念或幻想轻生,看起来自相矛盾(所谓的生之依凭亦是绝好的死之借口)。因此,我断定,人生的意义是至为紧要的问题。如何来回答它?对于所有本质的问题(我是指引人向死或向生的那些问题),只有两种思考之路径:一种是拉帕利斯式的,一种是堂·吉诃德式的。唯有实证与抒情的联姻,才能使我们同时求得情绪的感动与理智的明晰。对于这样一个既微末又沉重的话题,古典的学究式辩证法可以稍歇,它应当让位于一种更为谦逊的思考。这种思考出自于人类共通的同情与理解。
从前自杀仅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讨论,然而在这里,我们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个人思想与自杀的联系的角度来考虑。自杀这类行动,就像一件艺术杰作,在心灵的幽寂中酝酿打磨,本人则对此一无所知。终于,某一夜,他扣动扳机或纵身一跃。我曾听说过一个自寻短见的公寓管理员,自从五年前他痛失爱女,便性情大变,过去的阴影“侵蚀”着他。是的,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词了。开始思考即是开始被侵蚀。这与社会无关,阴影的蛀虫深埋在他的内心,病因当在这里寻找。人们需要跟随这条线索来理解这致命的游戏,一个人是怎样从面对存在的清明状态转而逃向黑暗的绝境。
自杀的缘由有很多,最明显的往往最不致命。很少有人(但不排除)经过三思而自杀。究竟是什么触发它,我们总是无法确证。报纸上总说是“切肤之痛”或“不治顽疾”。这些解释看起来可信,但必须弄清那绝望的人自杀当天,是否有朋友用漠不关心的语气同他交谈过,此君难辞其咎,因为这足以聚积起绝望者未决的忿恨和厌倦,使他坠入深渊。
倘使难以捕获那电光火石的一霎,因那微妙的步伐,心灵趋向了死亡,那么,从行为本身来推演其后果会容易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在剧情片中那样,自杀意味着供认不讳。自杀者坦承生命对于他来说是多余的,或是承认他不明了此生何为。我们不必在这种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日常用语中来吧。他只不过是坦承“不值得为生活殚精竭虑”。诚然,活着,从来就不容易。你一刻不停地在生存的操纵下做出各种姿势,原因有很多,首当其冲的就是习惯。自求解脱意味着你已有所觉察,哪怕是本能地体悟到习惯的荒诞不经,生命的空洞乏味,以及骚动之疯癫和痛苦之无谓。
那么,是怎样一种难以估量的感觉,剥夺了生命不可或缺的睡眠呢?一个能够被解释的世界永远是令人亲切的,无论这理由多么贫瘠。但相反的,当宇宙的光明与幻景倏然泯灭,人就会感到自己是流浪者和异乡人。往日家园的追忆已杳然不可追,许诺的乐土又无从期冀,这放逐已无可挽回。人被剥离出生活,演员脱离了布景,这大概就是荒谬的感觉了。毋须进一步解释,可以想见,对于所有想过自杀的健在人士来说,这种荒谬感与对死亡的渴求存在着某种直接的联系。
本文正是旨在探讨荒谬与死亡的这种联系,以及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自杀成为了荒谬的解药。我们可以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对于一个真诚的人来说,他所坚信的可以支配他的行动。那么,笃信荒谬就必然引发相应行为。人们有理由明白而不矫情地怀疑,这一重要性是否要求人们迅速弃置一种复杂的境地。当然,我指的是那些倾向于言行一致的人。
直白地说,这是个看起来既简单又棘手的问题。
但是如果认为简单的问题答案依旧简单,明晰性指向明晰性,这样设想就错了。由因及果地演绎这个问题或反向为之,如同人自杀还是不自杀一样,只有两种哲学式的解答,是或否。这看起来太容易了,但我们仍需考虑到那些持续追问却不下结论的人。这里我不是在嘲讽,他们才是大多数。我同样注意到一些人口中答“否”,行动起来却像“是”。事实上,如果我采纳尼采的标准,无论如何,他们想的都是“是”。
相反的,那些自杀者常常是确信了人生意义的人。这样的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在需要逻辑的地方,矛盾才变得如此尖锐。将哲学理论与它们的宣扬者作比较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些不承认人生有意义的思想者中,除了属于文学的基里洛夫(Kirilov),属于传说的波勒格里诺(Peregrinos),属于假想的儒勒·勒基埃(JulesLequi—er)之外,没有人执守逻辑到为此舍弃生命的地步。叔本华常被人当做笑柄,因为他坐在满桌山珍海味前盛赞自杀。这可不是用来开玩笑的。这种嬉笑着面对悲剧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据此我们可以看清一个人。
面对上述种种牾牾与费解之处,我们是否可以下结论:一个人的人生观与其弃世行为并无联系?我们还是不要在这点上夸口吧。其实,在人对生命的眷恋之情中,有一种比世间一切苦难更为强大的东西。肉体本能地恐惧灭亡,它的判断应当同精神的判断并驾齐驱。我们先有活着的习惯,再有思考的习惯。在日复一日奔向死亡的竞赛中,肉体始终是无可争议的引领者。简言之,矛盾的本质在于一种所谓“躲避”的行为之中,因为它差不多等同于帕斯卡所谓的“转移”。“躲避”是永恒的游戏。典型的躲避行为即是希望,这也是本文的第三个主题。那是一种愿景,渴盼另一种值得去过的生活,或是一种欺骗性质的幻景: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活,而是为某种伟大的理念。理念超越生活,升华生活,赋予生活意义,以至背弃生活。
这一切都使事情更加混乱。人们直到今天都在不遗余力地大玩文字游戏,并假装笃信:拒绝赋予人生意义即是宣称人生不值得过。事实上,这两种判断间并无固定的尺度。只不过,不要让上述的混乱、分离和自相矛盾迷乱了心智,让我们删繁就简并直奔主题。一个人自寻短见是因为人生不值一活,这当然不假,但它只是个妇孺皆知的空论。而这种对存在的侮辱,对人生的彻底否定,是否来源于人生的无意义呢?人生的荒诞性是否一定要通过希望或自杀来逃避呢?这是在拨开迷雾的同时需要厘清、探寻并阐明的。荒谬操纵着死亡吗?这更是第一位的问题,远超一切纷繁的思想路径和冷静的思维运转。在这种探寻和激情面前,意义的阴影,矛盾的柢牾,以及一个“客观”心智善于引入的心理学都应弃置一旁。这里只需要一种非公正的,换言之,逻辑的思考。这并非易事。合乎逻辑并不难,但要锲而不舍却几乎不可能。自杀的人借着感情执守到底。沉湎于对自杀的思考,我发觉到唯一一个使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直达死亡的逻辑?在此我指出推理的根源,只有借着适度的激情,依靠有真凭实据的探索,我才能寻有所获。这就是我所谓的荒谬的推理。很多人已经开始了,至于他们是否会坚持不懈,我不得而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