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细心察看我母亲脚上的牙印,在她眼前晃动手掌询问。母亲神志尚清,视力有些模糊。她在田里拔草时踩上了蛇,以为踩到了树枝或豆萁,只觉得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提起脚,脚上挂着什么东西,蛇!一边惊呼,一边本能地把脚一甩。队长疾速冲过来,循着蛇行方向猛追,踩倒大片的稻禾。拔节的稻禾枝粗叶茂,蛇瞬间无影无踪。没看清蛇,又不懂辨识牙印,只能待在田头“留观”。丁郎中说,可能蛇比较小,毒液不多,但耽搁了三四个小时,蛇毒已经漫到大腿了,蛇毒进入心脏就没救了。丁郎中的话,让全家陷入恐慌,此时我才明白,这绝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丁郎中示意我们回避,民间医生祖传的绝技是不轻易示人的。父亲去厨房做晚饭,吩咐我烧火。事后听母亲说,丁郎中拿小刀切开伤口,顺着腿脚按压,挤出毒血。用绣花针在伤口周围扎出几圈针眼,敷上药泥。药泥是捣烂的草药,母亲只记得其中有半边莲、丝瓜叶,其余的她不认得。那一夜,丁郎中留在我家,只打了会儿盹,此后不时过来探望。母亲每天皱着眉头大把吞下黑黑的药丸,大碗喝下绿色的草汁,折腾得只剩半条命。求生欲赋予她超乎寻常的平静和耐受力,痛苦的记忆让她的余生变得喋喋不休,包括因此受损的视力。
母亲一直“住”在囤匾里,吃饭不上桌,睡觉不上床,父亲曾戏谑道,要不把马桶也提过来?——当然,母亲已日见好转。囤匾是囤积稻麦的竹制农具,不知哪一辈的遗训,但凡病因古怪,小儿发烧,居然作避邪的居所。如同孙行者金箍棒一划,一切妖孽都被魔力挡在无形的圈外。囤匾有个难于书写的俗名,因了它的谐音,才被神化的么?乡俗神神道道,说不清。父母的启蒙中,无相关诠释。不过,一向严厉的母亲,目光里开始重现母性的慈祥,就连割草的催逼中,也多了一句温柔的叮咛:小心蛇啊。
母亲说的蛇,专指毒蛇。水蛇、乌梢蛇、大黄蛇都无毒,赤练蛇微毒,咬不死人,红黑相间的横纹漂亮得让人心怵。咬母亲的是蝮蛇,俗名“瞎眼皮鞭灰”,母亲固执地认为,这个俗名就是她目糊的最好注脚,她振振有词的观点影响了我多少年。事实上,蛇视力严重退化,跟瞎子差不多,它们敏捷的反应全凭头部的红外遥感。蛇毒多属神经毒素,其他毒蛇同样使人“瞎眼”。
小心蛇!这句话似一道魔咒,卡在我成长的咽喉。让我超前品尝人世的艰辛,以畸形的早慧思考生与死的命题。乡下孩子喜欢打赤足,田间小埂一层细密的嫩草,足底毛茸茸痒丝丝的舒坦能沿着双足传递到全身,而我不敢赤足。割草时,我以孩童少有的警觉审视草丛,竖起耳朵,时刻提防蛇冷不丁蹿起来,在我手指上留下恶毒的牙印。我不敢走夜路,机耕路和灌溉渠是田间“官道”,茂盛的豆萁从两边涌向路中间,谁知道它们盘伏在哪里,伺机向我进攻。夏天别人趿着拖鞋去看露天电影,我脚上是不可思议的布鞋胶鞋。家里的手电是奢侈品,不轻易用。与父母一起赶夜路,我闹着点桅灯。孩子间流传着一句俚语:狗咬一蛇咬二。意为狗反应快,咬走在最前头的人,蛇不同,第一个惊动它,第二个遭殃。他们能举出好多道听途说的例证,推三拉四缩到队伍后面。按他们的逻辑,放单是不会遭蛇攻击的,但我依然不敢独行冒险。有次看电影掉队了,黑灯瞎火壮胆夜行,我卯足劲冲过几条田埂。坑坑洼洼的小路,嘲弄着一个少年慌乱的脚步和怦怦的心跳。
我们和蛇处在同一个世界,却对它知之甚少。蛇为了生存,在进化中修炼成灵异之物,本身并无恶,恶是人强加给它的不实之词。多年后,我逐步抹去一个乡村少年的狭隘与偏执,却始终无法清除心里那道魅影。不说私愤,世人的公愤足以证明人与蛇势不两立,它邪恶如鬼魅,令人毛骨悚然又咬牙切齿。见蛇不打三分罪,不管谁招呼一声:毒蛇!附近的人都放下活计,提了工具奔过去,一条条蝮蛇葬身在铁耙锄头铁锹扁担的合力围剿中。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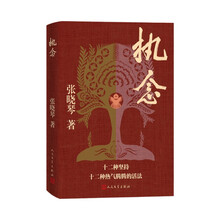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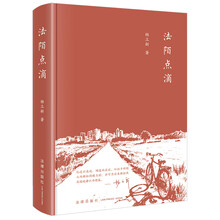
——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