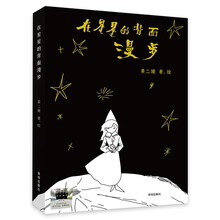这期间,我也结识了路易·阿拉贡和菲利普-苏波。阿拉贡比布勒东稍晚一点来到我的书店。
路易·阿拉贡那时正为自己的名字和八字胡的问题而苦恼。他绝对是我见过的最和气、最敏感的一个男孩。也是最聪明的。和他相处非常容易。他热爱诗歌,但不追求过多的不羁。初认他的时候,他还在读医科一年级,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魏尔伦或拉弗格的诗集,非常不习惯他的同志们的那些粗俗言行。还记得我们最早的几次交谈,他跟我说心里话,那些他在阶梯教室里听到的荒唐的诲淫话,差点让他流眼泪。
他已是一个绝顶健谈的人。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三个小时,带着那种轻微的鼻音——在我看来,这正体现了他的那种讥讽的方式:布袋木偶的挑战,戏谑式的疯狂。有时候苏珊娜·博尼耶下午三点左右离开书店去买东西,六点钟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还站在原来的位置,玻璃橱窗的门洞里,沉浸在毫无停顿倦意、意兴飞扬的谈话中。
有一天,他跨进门,手里拿着浅色的手套,应该是在附近有一次较为正式的拜访。可在时而电光火石、时而细流涓涓的谈话开始后,他把这次约会忘得一干二净。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过来(他随后介绍说,那是他的大姐),很粗暴地打开门:“嗨,路易,我可等了你两个小时了!你是不是疯了?” 我们都很喜欢阿拉贡,也很自然,一直确信他将成为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我似乎是一九一七年认识菲利普·苏波,但已记不清初识他时的情形。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将他与布勒东、阿拉贡联系在一起;他们三人不知在哪里相识的。但有段时间,我看到他们三人总在一起,为某项共同的事业非常团结。
苏波是三个人里,最优雅,也最有锋芒的一个。
他的攻击性显得不那么自然;细想下,那也是自然的,只不过在他身上,更近似一种神经质——神经质磨砺出了锋利的瓜子。可他又是有情有义、很有教养的人,这两种品质又相辅相成。于是,他总是伤自己胜过伤他人,并导致他最后向社会开战。我暗地里想,最初的时候,可能他是最英勇无畏的一个。
阿拉贡,似乎也并非生来就喜欢战斗,可他一旦进入状态,便很享受那种激烈,特别当有人懂得对他施加一种几近父亲式的权威领导,且不断给他鼓励与肯定的时候。他披着一副漂亮的文学铠甲,在战役中所向披靡。
这是后话了。我在此要讲的,仅是达达主义,以及《文学》刚创刊的时期。
这本杂志的第一期于一九一九年三月面世。同一个月里,奥岱翁街有一场音乐盛事:萨蒂的《苏格拉底》试演。这一出是埃德蒙·德·波利纳克公主模仿昔日的领主,独家定购的曲目,此前只在公主府上演出过。因此,在我们这里的演出也可以算是首演了。
苏珊娜·巴尔格里克——歌声绝妙无比——一个人唱了全部曲目,着实厉害,那作品原是为三种女声写的。萨蒂本人弹钢琴。让·科克托主持。
为了集中相对比较大的受众面,我们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这天组织了两场演出,分别在上午和晚上。大家都知道晚上,弗朗西斯·耶麦正巧路过巴黎,他会来,而纪德和克洛岱尔也会来。
上一个月,科克托在我们这边的一次小型集会上已初露锋芒,对于那次集会,我并不很满意。那是《好望角》的朗诵会,关于这一作品,我得好好来讲讲,以泄长久以来未充分表露过的真实感受。
天晓得我对科克托是喜爱的,也很欣赏,甚至现在比以前更加欣赏他。那时候的他,可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无疑,他是个诗人,在我看来,其散文诗更甚于韵律诗。因为他的散文诗很有自己的风格,带着一种伪装的处子般的纯真,而他的韵律诗,由于每一句开头都有刻意压韵的字母,显得造作之极,令人生厌。说实话,他的韵律诗叫我头痛。很有可能,我这话讲得不公正,但当一个人头痛的时候,很难说话公正。
他在写《好望角》的时候,刚刚发现当代诗歌以及那些先驱诗人,放弃了《轻浮王子》和《索福克勒斯之舞》(——事实上那两篇中有不少出彩之处)。
他奋力投身于先锋运动,对此,得毫无保留地称赞:其天生的才能丝毫无损,同时,又赢得了新的徽章。
科克托从来都不是第一个冲进突破口,但却总是由他去插上战旗,话说回来——这事儿,也总得有人去做。
P108-111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