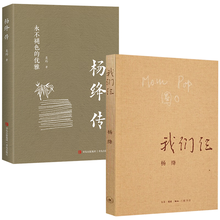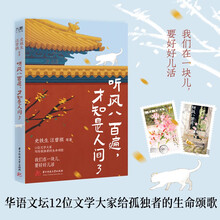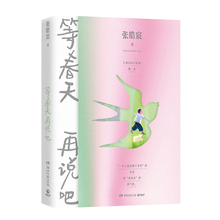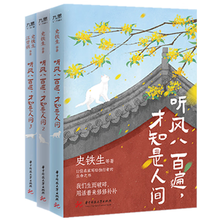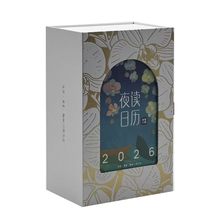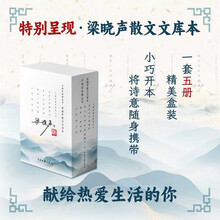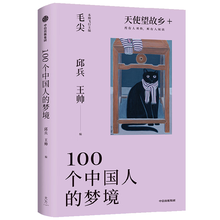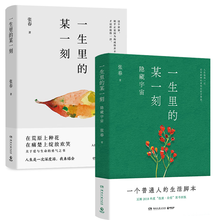天亮得明显晚了,但身体中的太阳照常升起,一如既往准确,如格林尼治或紫金山,没有季节转动之差。五点钟,或稍早,四点半,体内太阳便升起,与自然界的太阳不同步。醒时一片黑暗与天色微明感觉很不相同,你醒了,大地还没醒,怎么办呢?开灯,照明,却像是昨天晚上的感觉,没有结束便开始吗?
[2012-09-1406:12]
五点钟的夜,四点半的夜,四点,身体醒来,天空和大地都还未醒。有祷告习惯的人还是好,这时有明确的事可干,可像清水一样洗涤精神,如同洗涤有诸多睡垢的身体—残梦、破碎的意识等等。但若无信仰,内心也没任何语言,就什么也没有。没有超验,没有头顶上的事物,这时怎么可能有语言?只能喝茶。
[2012-10-0205:38]
为什么面对老建筑,会多少有点像面对自然界的事物?时间赋予它们生命。老建筑或老城市附着了时间,而时间恰是一切事物活性的媒介。自然界有着生生不息的时间,越老的城市、越老的建筑就越有时间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反对城市。但为何我面对窗外哪怕是早晨的小区也毫无感觉?因为太新,我倒成旧事物。
[2012-09-1806:23]
一天都在锋利地追逐,在水中,在晃动的草中,感觉追上了影子般的鱼。许多鱼都在刀下,瞬间分解,但不是最终的鱼。最终的鱼几乎不是鱼,非常孤独,只能看见影子般的尾部。为了这条莫须有的鱼,你精疲力尽,毫无胜利感。一切都到了最后:最后的鱼,最后的你,或许那最后的鱼不过是你的影子。
[2013-01-1421:35]
第一场春雨,淅淅沥沥,季节轮回之声,异常亲切。听觉似乎比视觉要古老得多,生命在声音中可抵达史前,譬如这淅淅沥沥之声。亿万斯年声音没变,而眼前的一切已变得不可思议。视觉与听觉的方向是相反的,分离的,在疾速城市化的今天尤是,这也是人们感到分裂的原因。我们的城市还有统一的视觉听觉吗?
[2013-03-1207:29]
密度与速度,造就不同的作者与读者,分水岭大体也在此。速度与故事密切相关,成正比,越快越好看。密度与故事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若即若离的,而总的倾向是疏离故事,通常成反比,密度越大,速度越慢,读者越少。所谓密度是作者通过故事承载的东西,他并不着迷于所精心设计的故事,而是着迷于故事的所有缝隙。
[2013-03-2908:09]
“注释”如果有了叙事功能、话语功能、切换功能,就会成为新的虚构空间,小说将会变得立体,具有透视性。然而批评家对此变异远不如作家敏感,也没什么兴奋,由此看出二者的不同。我们太缺少式主义批评家了,缺少多样性。作家一味写实,讲故事,批评家一味解读内容,还是社会学的底子,太单调了。
[2013-04-0708:11]
让有密度的文字清澈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越有密度越应清澈,这样才会变得神奇。清晰而缺少密度,单薄;有密度而泥沙俱下,优于前者,但终缺少神奇与叹为观止的感觉。像今天,天好得让你望洋兴叹,读一些经典就像读这种天气,读远山,云,以及整个维度。没有密度的清澈不是真的清澈,天也一样。
[2013-04-1318:18]
一切都如此浩茫,时间,空间,在你动起来时也动起来,如此神奇,一棵树会与同一棵树对话,隔着时间,多年自己成兄弟。
[2013-05-1307:26]
最愉悦的是,在某一点上发现了更深的东西,于是开始驻留,细品,此时作者的驻留其实也是读者的驻留。这样的驻留越多,品质就越坚实,迷人,以至会有通灵的感觉。这里注满了时间,时间含量极其丰沛。我喜欢那些饱含时间的小说,当我身体中充满时间,我愿以阅读和写作方式探索它们。
[2013-06-2407:36]
一个人有时很难诠释自己,任何说出的都不及写出的,或想要写出的,任何的说出都是遮蔽。你的诠释不可能比你写出的更好,就像在山顶上不可能再造一个山顶。甚至在山顶上支个凉棚也不可能。
[2014-01-1915:45]
降调,示弱,在沼泽地的叙述中,是一种叙述的推力。所叙述的内容打上这种低调的目光,再平凡琐碎也可读。若无任何变调,强行持续叙述就会平庸,乏味,难以卒读,是无效写作。所以有时变调是一种困境中的选择,虽然这时仍可能还没找到叙述的方向或目的,仍在沼泽中。
[2014-02-1618:57]
以为快要走出叙述的沼泽地,结果再次陷入沼泽。读者只能忍受一次沼泽,二次落入就只会剩作者在那里。孤立无援,艰难,无意义,这时干任何事情甚至散步都带着恐慌色彩。卡夫卡为什么打动人?就是常描写这种恐慌,某种深层的东西导致的表面的荒诞行为。把一杯水喝掉,接着又喝了一杯,但根本不渴。
[2014-02-2209:19]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