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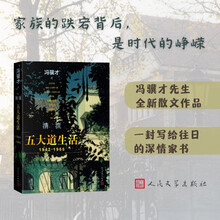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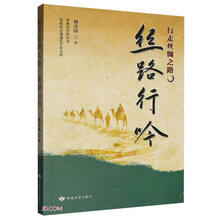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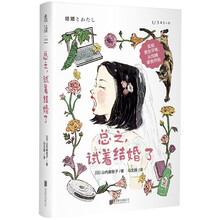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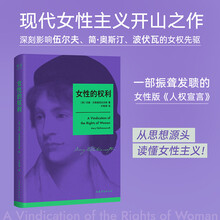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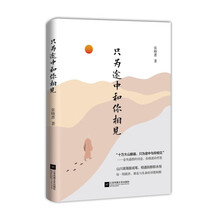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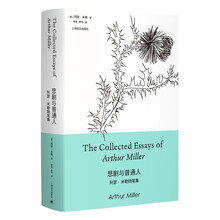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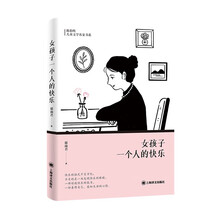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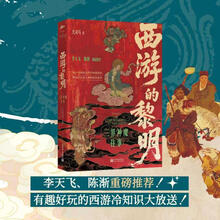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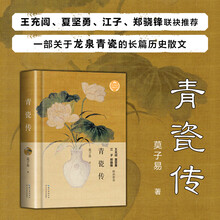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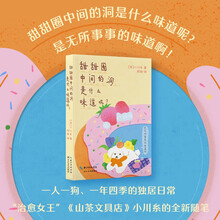
u 「菜场女作家」陈慧首部“村镇女性故事集”
继《在菜场,在人间》后又一部人物群像佳作,以泥土般质朴的笔触与月光般温柔的凝视,讲述中国小镇女性的生活和命运。
u 一部平民视角的女性生存实录
从市集街巷到农家院落,从邻居、顾客到母亲、姐妹,照见「沉默的大多数」女性群体的生存面貌。不编织田园牧歌,不贩卖苦难美学,以粗瓷碗盛白开水般的笔调,还原汗渍浸透的生命肌理。
u 见证平民女性的命运交响
有的人尽力用围裙兜住孩子的饥饱,有的人试图用一生寻找婚姻的支点,有的人不得不用双肩担起生计与尊严——在「她们」与「我们」的镜像叙事中,铺展中国乡土女性代际传承的生存图谱。
u 见证市井哲学家的微观史诗
当知识分子的女性主义悬浮于空中,这位混迹菜场二十年的女作家,用沾着泥点的笔尖,写下最朴素的女性力量——那些被认为「没文化」的女人们,早就在讨生活的扁担两头,托举了整个家族的春秋和中国乡土的月亮。
u 质感双封,胶版纸印刷,阅读友好。
《她乡》是一部真正由平民女性书写、看见平民女性生命的群像故事集。继广受欢迎的《在菜场,在人间》后,「菜场女作家」陈慧再次回归人物叙事,以泥土般质朴的笔触与月光般温柔的凝视,讲述中国小镇女性的生活和命运。
在江苏平原的村庄、浙江小镇的乡下,作者目之所及的女性大多过着朴素而沉默的生活。她以筛米粒般的耐心,筛去猎奇的稗子与矫饰的秕谷,如实写下她们的喜怒哀乐,让她们不再是陌生的剪影,而就像是读者身边的某个女性长辈或女性友邻。
作者写“她们”的故事——邻居、朋友、顾客、同一个菜场的小贩,也写“我们”的故事——我、养母、奶奶、姑姨和姐妹……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平民女性可敬、可爱、可怜、可感的多种样子,以平等的视角记录下生命与生活的本真。
养母
她说:“你不知道哦,我和你爸结婚好几年总是怀不上,你奶奶眼睛盯着我,你外婆心里忧着我,村里村外的大娘二婶子在我背后长长短短地议论着。我心里也着急,可急也没有用啊。去过的庙堂,拜过的菩萨,几双手都数不过来;中医的汤药、西医的药片和郎中的偏方,听到什么有效就吃什么。河对面的四爷爷,你还记得吗?他家的儿子叫升儿,虽
然他比你大不了几岁,可按照辈分来,你得喊他一声叔呢。有一年,我喝你升儿叔的尿。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去你四爷爷家敲门,接上一碗你升儿叔起床后的第一泡尿。那叫童子尿,又黄又骚。我眼睛闭着,不去闻,不去想,憋着气咕咚咕咚地喝。喝完了,擦擦嘴,一天之中最大的坎儿就算是跨过去了。”
我听得背上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觉得太不可思议:“那么恶心的尿你也喝得下去呀?多愚昧!”
“那怎么办?喝不下去也得喝呀。”她扯了扯嘴角,估摸着是想笑一个给我看看。可是,浅浅的笑意仅仅在两颊上艰难地挣扎了一下就没了影儿。她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前后喝了两三个月,喝得我饭也咽不下去了,脖子上瘦得只剩下三根筋,走起路来两条腿软绵绵的。”
我坐着,不出声。一向能言善道的我,此时此刻,竟然没办法吐出只言片语。我看着她,她的眼神穿过堂屋的门,定在院子中某个虚空的点上。金色的阳光从半空中倾倒下来,兜头兜脑地浇在院子中央的银杏树树梢上。于是,银杏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像是镀了一圈薄薄的金边。好一会儿,她才冲着我笑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是怎么挨下来的。后来,还是你爷爷奶奶松了口,说生不出就生不出吧,去哪里领个孩子回来养着呗。”
我来劲儿了,笑嘻嘻地问她:“所以,你一下子就和我接上头啦?”
“哪有那么便当?”她摇摇头,“前后看了好几户人家呢,男孩女孩都有,都不太中意。稍微大点的孩子记得自己的妈妈爸爸,怕养不熟;刚刚生出来的,软塌塌的,我瞧着心里没底,不敢要。你刘家庄的姨外婆给我介绍的一个男娃儿,才几个月大。大六月的天,热得冒油哇,我和你爸爸赶了几十里路过去一看,是一对双胞胎中的老大,长相倒是蛮好,眉清目秀的。我刚往手里一抱,他就哇啦哇啦地哭得山响,哭着哭着,他的小肚脐眼慢慢地像个鸡蛋一样凸出来了。我心里那个慌啊,压根儿不想往回带。”
我有点幸灾乐祸,逗她:“在农村,男孩可比女孩金贵。你咋不乐意要呢?”
她也笑:“哦哟,什么金贵不金贵的,男孩女孩不都一样?过了没多久,又有人上门来给我说了个女孩子。路倒是不远,河东村的。那孩子命苦,还不会走路,她妈妈就生病没了。那个女孩皮肤白白的,嫩得跟一方水豆腐似的。”
“真有那么漂亮?”我的语气酸溜溜的,“那你为什么没把她领回来当女儿?”
“没敢要。”她老老实实地交代着事情的来龙去脉,“她的外婆是咱们村的,从我们家往东数第四户,有两个五大三
粗的舅舅。我在人家几口子的眼皮子底下养着那个小姑娘,得多紧张多小心翼翼?再说了,我胆子小,她妈妈不是过世了吗?万一她不放心自己的女儿,隔三岔五地托个梦啊显个灵啊什么的,不吓人?”
我咯咯地笑,搂着她的脖子晃来晃去:“你这个不中意、那个不喜欢的,最后,我就成了你的女儿啦!”
“是呀。”她由着我搂着,一动不动地沉浸在往事里,“公社的妇女主任和你妈妈是朋友,她说你爸爸在部队里当兵,一年到头就只有几天的探亲假。你妈妈一个人在家拖着四个孩子,大的一个十三岁,下面三个小的都还在拖鼻涕水,没一个帮手,起早贪黑种着好几亩地,实在是苦不过来。我一听,心眼就活了,挑了个日子叫那妇女主任陪着去了你家。你瘦瘦的,小脑袋上揪着一根冲天辫,脸蛋擦了煤灰似的乌黑发亮。午饭桌上,你坐在我旁边,我低下头逗你,拉拉你的小黑手悄悄地问,叫我一声妈妈好不好?你也不认生,小嘴一张,软糯糯的一声‘妈妈’冲口就出来了。妇女主任在桌子底下扯扯我的袖子,偷偷地取笑我:朱玉林,你羞不羞?我把你抱到我的膝盖上,心里美得不行。嗐!有什么好羞的?我终于有个女儿啦!”
我想了想,又问她:“我被你带回家的时候就没哭?”
“没哭。”她肯定地说,“你一点没哭,乖巧地靠在我的怀里,好像你生来就是我的孩子一样。”
她说这些,我一片茫然,因为我叫她妈妈的时候只不过两周岁多一点,讲话都不太利索。而我脑海里储存着的与她相关的最初的影像是黑白两色的:一大批家用缝纫机整齐地排列在一间宽敞的大房子里,而那些静止不动的缝纫机中的某一台,是她的。
很奇怪,即便在我成年之后,这个概念一般的场景仍常常出其不意地穿插在我的梦里。有时候,我甚至不敢确定这一幕究竟是自然而然地根植在我的记忆里,还是我有心提炼自她后来的讲述。但我很肯定,与童年相关的某些碎片之所以能如此清晰地回放,一定是彼时那个小小的我,深刻地快乐过。
在磨头镇绣花厂所有女工都坐在缝纫机前埋头苦干之际,我和另外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在厂房的过道里自由玩耍。缝纫机面板的四角硬邦邦的,我玩着玩着,脑门儿就磕到了其中的一个角上。于是,一边哭,一边晕头转向地找到她,伏在她的膝盖上求安慰。她说,你乖着呢,不爱痴哭,给你揉一揉撞疼的脑门儿,你马上不掉眼泪了。绣花厂离家有三十多里路,来去不便,她带着我在厂里住过几宿。宿舍很简陋,睡觉的床是用两张高脚凳和两块木板依着墙壁拼起来的。她说,半夜里迷迷糊糊地伸手一摸:身旁是空的——小小的我已经滑到了“床”与墙壁之间的缺口里去了,就那样站着呼呼大睡。
她说给我听的这两桩小事,我像是身在其中,又好像不得要领。她的“说”像一支橘黄色的蜡烛,飘忽、温和地照亮着我人生之初的一段记忆。但当她停下了,不说了,那些久远的、细碎的童年旧事又像退潮的水一样,退到我目光难以触及的地方。我真真切切记得的只有一碗馄饨——她为我讨来的一碗馄饨。
磨头镇的老街上,离绣花厂不远的国营小吃店里,冒着热气的大铁锅前,一位身材高大、系着白围裙的中年男人正忙碌着煮面条、煮馄饨。他右手边的桌面上摆着一溜儿蓝花碗,碗里是浓如奶水的骨头汤,汤面上漂着翠绿的葱花。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中年男人手里的竹笊篱,笊篱在铁锅与蓝花碗间不停地穿梭。锅里的面条和馄饨捞到碗里,碗里的面条和馄饨又被跑堂的胖大婶搬到吃客面前。吃客的筷子在碗里一搅拌,丝线一样的面条和白玉一样的馄饨馋得我直咽口水。
那一天,绣花厂放工了,她带着我去小吃店吃了一碗馄饨后准备回家。馄饨里有一块指甲大的嫩肉,实在是太鲜美了!尽管一碗中的大半进了我的胃袋,我却说什么也不肯离座,闹着吵着要她再买一碗。她的钱袋里只剩下 9 分钱,馄
饨要 2 角钱一碗,国营的店又概不赊账。可我不管,我非吃不可!没办法,最后她不得不壮起胆子去找煮面条的师傅讨来了半碗。
不管是谁,但凡沦落到低声下气去讨东西的地步,免不了要受些委屈。年轻时的她,脸皮薄薄的,与人讲话从无高声。可为了我的无理要求,宁愿赔着笑听那大师傅冷嘲热讽一顿。三十多年后,已为人母的我对其时的她颇有微词,扬扬得意地向她展示我的教子方:“我的小孩要是敢不讲道理,打他一通屁股就老实了。你倒好,明明是我不听话,你反倒
去滋长我的坏脾气。”
她呵呵地笑,慢悠悠地来了一句:“我就是舍不得打你呀。”我一愣。“舍不得”这三个字钻进耳朵里,瞬间衍生出万千滋味。是的,我做了她十年的女儿,她没有动过我一根指头,即便是言语上的责怪,也少之又少。奶奶和我咬耳朵:你妈妈呀,就是个韧面筋。
在老家那块,“韧面筋”这一称呼多少带着点贬义:性子慢,做事拖拉,不带劲儿。奶奶对她的点评很到位。她确实不是撸起袖子就能风风火火下地干活儿的好角色,她只会坐在家中缝纫、绣花、做鞋子。她的这三样手艺在我的身上展现到极致。我的帽子、手套、鞋子、衣服、书包通通出自她的手,无一例外被她绣得红红绿绿。花花草草、小猫小狗、星星月亮之类的,她绣什么像什么。村庄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聚起来,人也不少,要数她的十指顶灵巧。滑雪衫刚刚流行起来的那年,她就兴冲冲地去县城的百货大楼扯回了料子,为我加工了一件双色的滑雪衫。正面是大红的,反面是湖蓝的,银色的拷纽亮闪闪,正反两面能换着穿。八十年代的乡下,这种样式的衣服还是极少见的。可以这么说:穿上那件滑雪衫,我就是乡里最潮的妞儿。然而,她的灵巧似乎仅仅局限于指尖上的精细活儿。作为娘家的长女(外婆生了五个女儿,她排行老大),婆家唯一的媳妇(奶奶生了七个孩子,一男六女),她居然不会下厨。锅里的油烧热了,她还在紧张地东张西望;好不容易把菜推下了锅,她又发愁该先放哪种调味料;手忙脚乱地炒了几下,盖上锅盖焖着后,终极大问号又来了——怎样才叫烧熟?
家庭主妇煮饭做菜,除了天赋,其余全凭感觉和习惯,你叫别人怎么回答她?这个女人这样讲,那个女人那样讲,讲来又讲去,她依旧一头雾水。她脾气“韧”,毫不介意别人的揶揄,大方地承认自己厨艺上的失败。奶奶在时,大树底下好乘凉,她心安理得地不进厨房;奶奶离世后,每逢过年过节姑姑们来做客,她讪笑着声明她只负责提供食材,不负责做饭。她心眼实诚,不管多好、多贵的东西,只要家里有,她都舍得拿出来招待大家。她的慷慨抵消了厨艺的缺憾,所以尽管她连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都捣鼓不出,姑姑们对她的评价还是挺高的,一致认为“朱玉林人不错”。
等等......
她们
003 命
024 玉坠
039 杨梅干
049 单刺仙人掌
062 眼泪
073 无相
085 哑巴姑娘
094 菠萝头
106 阿妮和她的狗
我们
123 养母
151 奶奶王成英
169 我妈的私房钱
181 姐姐
196 婚姻的支点
202 姨奶奶
217 大姑妈
224 姑姑的鸭蛋
229 后记 每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