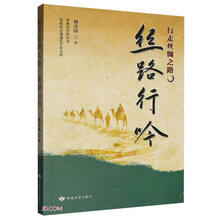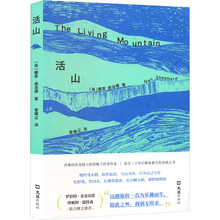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海楼小集:边走边看》:
在中国这个注重诗文传统的国度里,除了像“文革”那样的时期外,读书做学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知识分子自己深深地怀疑。几乎每个青年学人的身边都有同行下海(投海?)或另谋他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空前的大逃亡景象。
然而,读书做学问在古代知识分子那里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左传》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正是扬名后世的一种重要途径。
不过,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是现实主义的,他们注重现实的幸福,支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是没有天国的精神世界,死后的事情更难以预料,所以他们不仅求身后之名,更求生前之名,希望能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辛弃疾的词句“了却君主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人生态度。不过,现实的幸福难以预期不说,还是易朽的。这样,身后之名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人生局限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救助之道。学问对古代读书人的意义是双重的,它又往往是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因为应付科举考试需要学问的根底,并且在注重诗文的官场,它对职位的升迁也不无意义。也就是说,学问不仅可以使他们获得身后之名,而且可以赢得生前之名。司马迁受宫刑后,现实的幸福已经没有可能,身后之名寄寓着他的全部希望,他发奋著《史记》,以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对“名”如此执着呢?这种文化心理深受原始的巫术观念的影响。
胡适在作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名教》中就指出,中国人对于“名”的信仰源于古老的迷信。日本的中国文化学者森三树三郎在《名与耻的文化》一书中对此做过进一步的分析:“原始思维的特点之一,是认为‘经常接近的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物和它的名总是如影随形,因此,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不是‘名表现体’而是‘名即体’。”因此可以说,人死后,只要他的名字流传下来,为人称颂,他就可以凭另一种方式存在,也即是“不朽”了。
现代人接受了唯物论(至少是对死的唯物论),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身后之名已不再能给他们以安慰。在现实生活中,学问也不再能使他们春风得意。
德国文学批评家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把诗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比作捡垃圾者。“捡垃圾者”一语道出在精神领域从事创造性劳动,而与市场无缘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在现代社会里,许多歌星在台上一曲千金,科学家带着发明专利走向实业,实用性强的学科研究者不断寻求和市场接轨。与市场无缘的是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从事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他们和一部分艺术家一起固守着人类最后一点尚未被商品殖民化的精神尊严,也因此一贫如洗。
做学问对个体的意义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罢了,与钉皮鞋、卖酱油一样,只是钱挣得更少。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同行们还承受着生活重压。
一个也在高校任教的朋友,住在一间八平方米的平房里,老婆气管有病,怕煤烟,不能生炉子,冬天屋内冷得像个冰窟。他曾踢着装书的几个大纸箱,愤然说:“要这些书到底有什么用!”他说只要给他两居室的房子,学非所用,也在所不惜。连起码的思想空间都没有,学问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显得太奢侈。况且,做学问一点都不比干别的轻松,它需要献身精神和持久艰辛的劳动。既然如此,苦守学问还有什么意义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在职业上尚未定位的青年学子开始了他们的逃亡历程。
告别学问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些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精神上的归属感。前年去海南开会,遇到一位投身商海的文学硕士。他已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了,来拜访和笔者住在同一房间的他的同窗。同窗仍在内地的大学教书,送给他一本在学术界小有名气的专著。他翻看着书,说:“我将来还准备回去。”他到底回去不回去,回哪去,我不得而知,但我感到他的心里有些不平衡了。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否还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名”的情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渐趋定型,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的待遇自然会得到改善。在学问失去对个体的终极意义又不能带来现实的福祉时,学问之路注定是一条精神上的漂泊之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