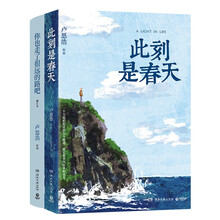白 夜 之 旅
面对着七色缤纷的世界地图,我常常会久久地发愣。地球原本是一个浑然的整体,海洋、大陆、岛屿、冰川,没有什么有形的界线分割它们。人类本来可以自由如天上的飞鸟,如水中的游鱼,如来去无牵挂的风,随心所欲地把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作为旅行的目的地,只要你拥有抵达这目的地的能力。然而人类描绘的地球并不是一个浑然的整体,色彩斑斓的地图上几乎汇集了世间所有的曲线,为的是用来分割陆地和海洋,用来限定国界。地图上的一种颜色,便是一片名称不同的国土;一种颜色,便代表一种语言、一种风俗、一种气候,代表人类极小的一部分历史。世界的丰富、复杂和神秘也许就是由此而来。
数不清地图上有多少国家。有些小国在地图上小得就像一粒芝麻,而大国却覆盖着整整一片大陆。目光在地图上旅行时,脑海中总会相应浮现斑驳的画面,有时清晰,有时朦胧,有时则空白一片。我的目光常常停落在北方那最辽阔的一片土地上。这是一片遥远而又熟悉的土地,我曾经无数次在诗歌和小说中阅读它,曾经无数次谈论它,也曾无数次用自己的想象来描绘它。想象它冰天雪地的漫长冬天,也想象它短促而奇妙的夏天,想象夏日那童话般的白夜……这片辽阔的土地,是苏联。
这几年经常接待来访的苏联作家,这些来自北方那片辽阔土地的苏联同行,不断地使我产生亲切感,每次分手时,苏联的朋友必然会说一句很真诚的客套话:“希望你能够到苏联来访问。”这当然也是我的希望。不过这希望似乎和那片辽阔的土地一样遥远。
希望终于由远而近。今年6月,应苏联彼得格勒作家协会的邀请,我和上海作家肖岗、郭在精组成一个小小的代表团,踏上了出访苏联的旅途。我们选择的季节非常好,在苏联的北方,白夜正开始降临,濒临芬兰湾的彼得格勒,是体验白夜奇观的最佳去处。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暂时消失了黑夜的地方。
1991年6月17日 北京—莫斯科
下午4点50分,北京晴空万里,炎阳灼烤着大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客机呼啸升空,飞行方向西北,目标是遥远的莫斯科。
乘坐这趟班机的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只看到一个身穿印有“澳门”字样T恤衫、留着大胡子的白人青年,从候机室漫长的等待一直到登机,他一直默然静坐,显得十分孤独。飞机起飞后,那白人青年便开始闭目养神。
因为机舱里都是中国人,所以气氛很轻松,到处是笑语喧哗。在飞机后舱,一位搞航空产品贸易的老先生,一边喝着又浓又稠的番茄汁,一边抚摸着胖鼓鼓的腹部,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现在呀,年轻人朝美国跑,老人都朝苏联跑。你看看机舱,不都是老人!”我扫视了一下机舱,并未产生同感。乘客中确实有一些年龄较大的中国人,但更多的是中年人,也有一些年轻人。
飞过蒙古时,机翼下只看到无边无际的沙漠,荒凉得如同月球,什么时候越过蒙古进入苏联领空,谁也说不清楚。而大地却由一片焦黄变成了深沉的墨绿,那是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叫不出名字的江河在绿色的莽原中流动,如同一条条巨大的黑色飘带……
进入苏联领空不久,飞机便飞经贝加尔湖上空。
贝加尔湖,这是个撩人心魄的大湖。在小说中,在诗歌中,在音乐里,我曾经许多次神游过这个碧水浩渺的湖泊,它令人想起那一段使中国人感到耻辱和伤心的历史。此刻,贝加尔湖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视野底下,轻柔的云烟在它的上空若有若无地飘动,森林和山峦用墨绿和青翠为她勾勒出优美的轮廓。湖水是晶莹的深蓝色,蓝得如同深邃的天空……没容我多看多想,贝加尔湖已从机翼下一掠而过。展现在前方的是俄罗斯广袤坦荡的大地。
飞机在空中飞行了整整九个小时,北京时间应该是18日凌晨1点55分,下降的飞机穿越浓厚的雨云,在莫斯科机场着陆。而此刻,却是莫斯科时间17日20点,这样,今天就比平常的日子延长了6个小时。走下飞机,夜幕并未降落,莫斯科正在下小雨,机场周围的白桦林被雨水浇洗得葱翠悦目。
在机场迎候我们的是苏联作协外联部的汉语翻译嘉丽亚。嘉丽亚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反应敏捷,说话的频率极快,这在会讲中国话的外国人中极其罕见。嘉丽亚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是“思华”,其中的含义无须解释。前不久她曾随苏联军事文学代表团访华,我们在上海曾见过一面。如今重逢在莫斯科,自然很亲切。嘉丽亚告诉我,这次上海作家代表访苏的全程陪同和翻译,将由她的丈夫米沙来担任。米沙是一位汉学家,苏联东方研究所的副博士。我想,有其妻必有其夫,米沙的汉语一定不会差。
乘车离开机场时,莫斯科刚刚开始被暮色笼罩。“伏尔加”轿车在宽阔的公路上飞驰,车窗外浓绿的白桦林扑面而来,这正是我想象中的莫斯科郊外。
嘉丽亚一路上不停地谈论着她对中国的印象,谈论着苏联作家对中国的看法。前些年苏联作家都想去美国访问,这几年作家们都争着去中国,许多苏联作家哪里也不愿去,只要求访问中国。这样便把苏联作协的领导们弄得很为难,毕竟僧多粥少,不可能让所有想访问中国的作家都能如愿。有些作家还为此吵架。我问嘉丽亚,苏联作家为什么对中国如此有兴趣?嘉丽亚想了一想,说出这样几点原因:一是苏联作家们对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非常感兴趣,想去看看;二是听说中国的轻工业日用品丰富而且便宜,想去买一点中国货;第三个原因最最重要,那便是苏联作家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晚上下榻在苏联作协的创作之家。这是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幢花园别墅,红色的楼房掩映在白桦林的绿荫中。米沙已在创作之家的大厅里等候我们很长时间了。这位50出头的汉学家已经谢顶,稀疏的黄头发下却有着一张年轻人的脸。他看着我的名片,居然准确地读出了印在名片上的每一个汉字,还用夸张的口吻叫道:“哦,您是团长!久仰久仰!”
创作之家的房间设施谈不上豪华,但很舒适。打开卧室的落地窗,夜风送来青草和艾菊的清香,还有悠扬的虫鸣。在卫生间亮如白昼的灯光下,竟然发现一只小小的金铃子,正停在墙角竖起一对透明的翅膀唱得起劲。听着金铃子那晶莹的歌声,身在异域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二十多年前在长江口的崇明岛“插队落户”时,我住的那间小草屋里常常能看见这样的金铃子,它们鸣唱的方式和声音也完全一样。
很好,在苏联的第一夜,将会有金铃子唱着歌送我进入梦乡。明天上午,我们将去乌克兰。
6月18日至6月20日 莫斯科—基辅
从莫斯科乘机,一小时后飞抵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三天美好的时光。基辅市闻名世界的佩彻尔斯克大修道院,市郊掩埋着被德寇杀害的20万无辜的巴比亚厄谷地,以及基辅市十月革命广场上数百人聚集正呈现出的民族情绪的骚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月21日 晴 基辅—彼得格勒
今天离开基辅赴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我们这次访问最重要的一站。在这里我们将逗留一周。
起程前抽空访问了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古老陈旧的高楼深院中,忙碌着无数编辑、导演、节目制作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和一位导演陪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演播室工作间,里面的设备显得笨重而陈旧。在苏联,电视工业的发展速度显然不快。因为严格控制进口,在这里很难见到日本或者西方国家生产的彩电,对一般的苏联人来说,彩色电视机是一种奢侈品。我们下榻的第聂伯河宾馆客房里,有一台20寸的黑白电视机,在楼层的门厅里有一台苏制的电子管大彩电,重达一百余斤,大概没有小偷能盗走如此笨重的彩电。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告诉我们,他们不久将迁入新的大楼,到那时,设备也将更新。“寄希望于将来”,这是当代苏联人的一句口号。
下午坐飞机抵达彼得格勒。专程从彼得格勒赶来陪同我们的63岁的老作家老米沙(为称呼方便,我们称莫斯科的米沙为小米沙),上午就急匆匆地在我们之前回彼得格勒了。他说他要赶回去修整他的苹果园,家中年轻的妻子在等着他。他答应在彼得格勒和我们见面。
在彼得格勒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彼得格勒作家协会外事处长、翻译家勃朗斯基。从机场到市中心,沿途的建筑颇为壮观。长达十余公里的莫斯科大街笔直宽阔,显示出恢宏的皇家气派。大街尽头,有巨大的青铜凯旋门,这是当年俄国军队战胜拿破仑之后为庆祝胜利而修筑的。市中心依然完整地保留着彼得堡当年的格局和建筑。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政府迁都莫斯科,彼得堡易名为列宁格勒。当时的苏联领导下了一道极具远见的法令,他们下令把彼得堡古老的城区划为禁区,在这个禁区里,不准建造新的房屋,所有旧建筑都必须得到保护。这道法令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展现我们眼前的,还是一个世纪前的彼得堡。这个大都市,如同俄罗斯一个最丰富的大博物馆,彼得大帝开创的业绩以及三个世纪以来俄罗斯辉煌的历史,几乎全部展现在这里。
我们下榻的莫斯科宾馆,正好在涅瓦大街的尽头,面对着涅瓦河,和著名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只有一街之隔。从我的房间窗户中能看到涅瓦河的波涛,也能看到对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在彼得格勒是家喻户晓,人们熟悉它,并不是因为其中的教堂,而是因为修道院里的公墓。自18世纪以来的大部分俄罗斯文化名人几乎都埋葬在这里,其中有文学家克雷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有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鲍罗丁、格林卡,有科学家罗蒙诺索夫,这些名字,都是苏联人引以为豪的,他们的造诣使世界对俄罗斯文化刮目相看。这些名字也是我所熟悉的,我的卧室和他们的安眠之地竟会靠得如此之近,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事情。这些俄罗斯的精英,我将一一拜访他们。
晚上,勃朗斯基代表彼得格勒作协宴请我们。菜肴很简单,西红柿色拉、烤牛肉,然而有啤酒。到苏联后,还是第一次喝到啤酒。自从戈尔巴乔夫下了禁酒令之后,苏联的商店里不仅没了伏特加,连啤酒也成为稀罕之物。勃朗斯基要了十多瓶啤酒,摆了满满一桌子。出访前,曾听到过很多关于苏联经济困难、日用品供应短缺的传闻,这几天我们亲眼目睹的现状,似乎要比传说的情况好得多。基辅的百货商店里,日用品还算丰富,饭店的伙食也过得去,而且价格便宜。我把我的看法告诉勃朗斯基,他苦笑了一下,诚恳地说:“我们的境况确实非常困难,你们住在宾馆里,不可能了解真实的情况。”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钱包,在里面翻寻着。我有点纳闷,不知他在钱包里找什么。一会儿,他找出几张印有表格和文字的小纸片儿递给我。在场的小米沙脸色严峻地把勃朗斯基的话译了出来:“这是政府发给居民的购物券,肉、糖、食油、烟,现在都要定量供应,有时候凭票也买不到东西。群众现在对前途都有些悲观,人们不想再听那些空话。”勃朗斯基的真挚和坦率,使人们都很感动。然而饭桌上的气氛却因此而显得有些沉闷。肖岗笑着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瓦西里安慰妻子的话来安慰勃朗斯基:“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他的江南普通话米沙听不懂,费了一番周折两位苏联人才搞懂其中的意思,于是大家哈哈一笑,只是笑得有些酸涩。
吃完晚饭已是夜里十点,走出宾馆,只见阳光灿烂,根本没任何夜晚的感觉。这时才真正领略到白夜的景象。穿过大街,想在这深夜的阳光下参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公墓,然而通向名人墓地的大门紧锁着,只能在围墙外的一片墓地里散步。这种时候穿行于墓穴之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窗外依然亮如白昼。小睡片刻醒来,已是凌晨两点,天光依然灿烂。推窗远望,城市正安然入睡,可是我却再也合不上眼。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