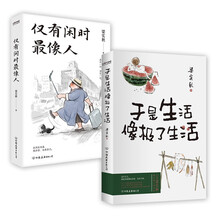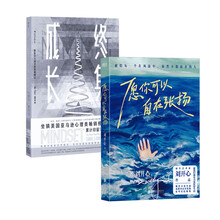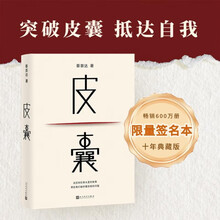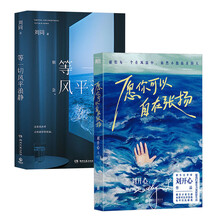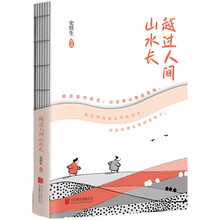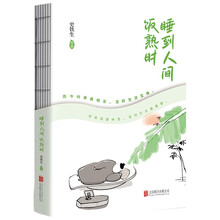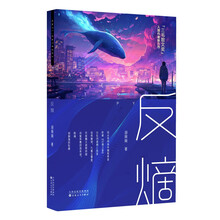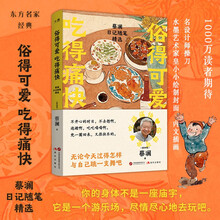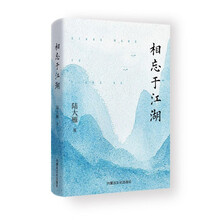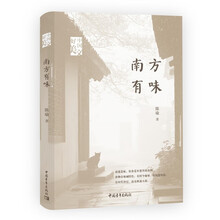写到大概第四条,也就是《Rap,说得下去吗?》那条稿件,吴彬提出要我写专栏,专论流行音乐。我没敢答应,迟迟疑疑半年,原因?觉得自己没那料。当时,生存的压力、时代的动荡已经开始明明白白冲击任何客观存在和想象中存在的书斋生活。以前天天读书、时时思考的状态,此时已离我甚远。1993年,我整天的记忆都是骑着自行车、搭着公交车、坐着采访车在外面乱蹿,然后回到报社立马可以就地写一些报道。读书的时间几乎没有,写作的日子更是难寻,这样的生活,让我没任何信心可以持续地写出供《读书》发表的文字。
但半年后想通了。灵魂实在感到饥渴和贫瘠,想拯救它。既然时间满载得心灵再无立锥之地,随时感觉要死掉,那么一个专栏的约定,岂不是给了它一个存活、生长的空间,有时间要长,没时间也要长?所以最后回过神了:这是我的运气,好歹得抓住。
1994年7月,“听者有心”开张了,第一篇的题目是“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印上了当年7月号的《读书》封面。
从此这么写下去。日渐练就一个本领:在路上、采访间隙、吃饭时间听随身听,想一些事,谋划文章的开头、结尾和中腹,灵机四时而动,文字全在脑中形成,在脑中修改数遍。有时候想得太妙,生怕忘了,随手拿笔涂写在采访本的边边角角,然后,寻得某一晚夜静无人,把它从脑中、从纸片上搬下来,复写到稿纸上。
定专栏名时,我对吴彬说:特别羡慕辛丰年老先生的“门外谈乐”,我也是“门外谈乐”,这栏名给我用该多好。
从“门外谈乐”想到了“乱弹琴”,就想以这仨字儿做专栏名。
写到那封信快结尾时想到了“听者有心”四字儿,加上去作为又一种方案。我记得还有其他方案,现在完全记不起来。
俗语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也是我的潜意识。我觉得流行音乐里能听到许多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那并不一定是作者、歌者所想,但是,就是有,就是真实存在,就是那么的丰富和有趣,所以,我有点儿像那么一个敏感的、有心计的、多心的、有时甚至歪心的人,想揭一揭你听不到和看不到的幕后潜台词。
专栏开下来,并不怎么自信,觉得自己是没练好的徒儿,匆匆上了台就开唱了,而且要一直唱下去。而《读书》的编辑也怪,从不给指点,从不给出题,后来也从不催稿。甚至,对稿子也很少改动。我写得战战兢兢,经常给吴彬写信念咕:自己还没修炼好,就要开唱了,如临深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