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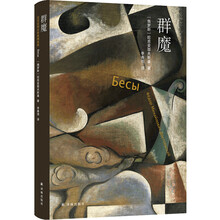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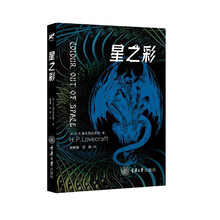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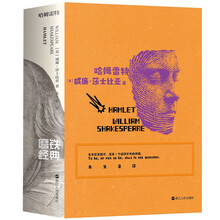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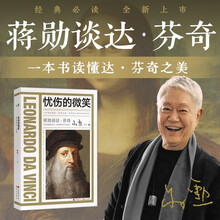

★谈笑风生,深思明辨。谈文学,也是谈生活。把评论写成美文,在批评中呈现性情。
★著名批评家李敬泽再致理想读者,从众声喧哗的会议室到寂静的远方山丘。
★“纸面之下还有一个广大的动荡的、很不清晰很不确定的层面。那是日常的思绪、情感、言谈,是生活和交往,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是思想的‘未封’状态。”——李敬泽
本书是著名评论家李敬泽的*新评论文集,收录作者自2014年以来有关文学艺术的各类评论、序跋、随笔和对话。这些文章广泛涉及中国文学艺术的前沿问题,见解独到精当,文采纷披斐然。内容既有对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总体性论述,也有对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细致剖析。
四年前,出一本书,名叫《致理想读者》。所收的是有关文学的文字和言谈。然后接着谈、接着写,晓行夜宿,雪落桃花开,四年来又零零碎碎攒下一本书,起个名字是《办公室与山丘》。
本来是想叫《知难集》的。语出《文心雕龙•知音》:“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章学诚《知难篇》申说此义:“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
刘勰、章学诚,千载同慨,说的是,知言难,知心更难,知言知心而又知人与人世者,又比更难还难。
这说的都是批评之难。或者说,做一个理想读者之难。从刘到章,反复申说一个“难”字,是在反复提醒我——我们这些以评论家或批评家自命的人——毋妄、毋欺,审慎、精进。成为他人之知音,成为天下之知音,这是何其难的事,难到近乎不可能,批评生涯就是在不可能中修行,求一线可能。
年来饶舌,在很多场合说到,我已是一个“前批评家”。这其中就有“知难”之意。是自知,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其实所知少、所见浅。我当然不至于写不出小说就宣布小说死亡,写不好批评就宣布批评无意义。批评意义重大,已经有很多锐气方张、身强力壮的才俊投入其中,驽钝如我,确实做不好,就该知难而退。所以,我真正想要的名字是“而退集”,我喜欢其中的一份诚实。
但最终,《而退集》也未用,编辑担心,这老气横秋的一“退”就退得没人读了。没人读我其实也不太在意,但又有明白人说:声称“而退”,结果还写了这么一大本子,这不是作法不自毙说话不算话吗?想想此话有理,所谓求诚而得不老实,遂放弃。
现在的书名是《会议室与山丘》。“会议室”好理解,无论在写实和隐喻的意义上,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的思想、言谈和文字都是在一个个真实和想象的会议室里展开的。他一直在参与讨论、与人对话。没有什么独语的批评家,没有什么作为自足的个人的批评家,他自身就是一个会议室,他永远敞开,永远在倾听、说服或者争辩。
然后呢,什么是“山丘”?那不过是李宗盛的那首老歌: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
还没能晓得 就快要老了
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
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
无知地索求,羞耻于求救
不知疲倦地翻越 每一个山丘
越过山丘 虽然已白了头
……
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等候
那一日,在车里听着这歌,忽然苍凉欣喜,不可断绝。当然我尚未白头,估计因为遗传也白不了头,当然我也不很在乎是否有人等候,除了无人等候你还等候什么?我只是觉得,生命中竟然是山丘连绵,永无尽头……
感谢我的读者。感谢我谈论到的那些作家。感谢书中的各位对话者。你们构成了我所在的会议室或论坛,我之所说也许是浅陋的,但从你们的声音里我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