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即裁剪。
——威廉·巴勒斯
我先期关于精神药物的著作,《文化之魔:瘾品社会》和《精神药物百科全书》,重点讨论了这些药物对人类文化历史的影响。我想消除一个荒诞不经却被普遍接受的认识,即“滥用毒品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本作品集所收录的最早涉及精神药物的文学作品是阿普列乌斯(Apuleius)创作于公元2世纪的《金驴记》(The Golden Ass)。然而,即便在古代,精神药物的使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史前学家已经发现,早在石器时代已有很多精神药物为人类所用。
人类使用致幻植物的最早确凿证据出现在约13,000年前。汤姆?德?迪拉哈依(Tom D. Dillehay)率领的考古学家团队在地处智利南部温带雨林中的蒙特沃德(Monte Verde)古人类遗址发现了一个棚屋的遗迹,看起来棚屋的主人是一位男性或女性药师,在屋里发现了20多种草药,其中两种据称具有致幻特性(茅膏菜和波耳多叶)。蒙特沃德古人类遗址也是公认最早的人类定居美洲的例证,这意味着,人类踏上新大陆时,已经对致幻草药有所了解。
然而,这个日期也很难说是最早的,如果要说考察人员正巧发现了人类最早接触精神药物的证据,这显然有些荒谬。事实上,把这段历史看作某个进化链条上的最后一节更合乎情理,顺着这根链条,我们可以返祖回到我们遥远的动物过去。因为我们不是唯一体验精神药物的物种——我们已知捕蝇伞菌的刺激性和致幻性,吸食了颠茄毒汁的蜜蜂也无法逃离茄属植物的魔力。如果我们真要找寻致幻状态的源头,那将会是原始时代,远远早于人类起源。
一方面,研究者注意到,动物会觅食这类物质,而人类使用精神药品的情况也引起了它们的注意。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在《鸦片:戒毒日记》(Opium: The Diary of a Cure)里写道:
所有的动物都对鸦片着迷。殖民地的瘾君子们深知鸦片对野兽和爬行动物的危险诱惑力。
苍蝇趴在盘子边缘神游太虚,带着小“手套”的蜥蜴吸附在吊灯上方的天花板上如痴如醉,等待天黑,老鼠爬到近前舔舐残渣。更不用说狗和猴子和它们的主人一样上瘾了。
马赛的安南人(即印支人)用特殊的工具吸食鸦片,以迷惑警察(一段煤气管、一个有洞的酒瓶和一个帽针),蟑螂和蜘蛛兴奋地围成一圈。
人类用动物来做药物实验,使动物喜欢上了这些药物。本书提到这方面的例子,如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塑造人类头脑的药物》(“Drugs that Shape Men’s Minds”)一文中证实,有些老鼠天生喜好酒精,而另一些则滴酒不沾,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在《醉蜘蛛》(“Drugged Spiders”)中提到蜘蛛在药物作用下不同的织网方式。动物不仅被人类喂食毒品,或自己觅食,它们本身也可能成为毒品源。日本人视河豚肉为美味佳肴,但也害怕中毒,很多东方的食客都深受其害。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在《海地僵尸毒》(“Zombie Poisons of Haiti”)中提到,河豚还有别的用途,海地的邪恶巫师们用河豚毒制成粉剂,用于将正常人变成僵尸。
即便是最高等的哺乳动物——智人——也和其同类一样无法摆脱永不餍足的寻求新刺激的欲望。在《惧恨拉斯维加斯:一场直捣美国梦的凶蛮之旅》一书中,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笔下疯狂的旅行者四处寻觅新鲜的肾上腺和松果腺。特里·索泽恩(Terry Southern)的小说《疯子的血》(“The Blood of a Wig”)讲述了如何获取一个分裂症患者的血。这些故事带我们走进一个把人血和人肉当兴奋剂的世界。尽管这些都是小说,但众所周知,蟾蜍的毒液里含有天然强致幻物5甲氧基二甲基色胺,而且很少有记载提到,人脑脊髓液里也有这种物质。有研究表明,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5甲氧基二甲基色胺[和另一种致幻物DMT(二甲基色胺)]的含量可能高于常人。
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验到意识层面天翻地覆的改变多半是不由自主的,但萨满巫师服用致幻草药却是有意为之。世界各地的萨满巫师——尤以致幻物丰富的亚马逊盆地最著名——试图让自己变形为动物以获取其他物种的能量。据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和他的追随者所言,这些做法是物种之间最真实的交流。这类变形在欧洲巫师中间也屡见不鲜,他们相信,通过涂抹用天仙子、曼德拉草和颠茄等致幻草药制成的“飞天药膏”可以变成鸟和兽类。《金驴记》描述了这种软膏的用法,女巫潘菲乐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猫头鹰。中世纪之后,寻巫者认为变形是魔鬼的障眼法,在质疑者看来,变形仅仅是幻觉。16世纪科学家约翰·巴普提斯塔·波塔(John BaptistaPorta,C.1535—1615)在《让人疯狂一日的方法》(“To Make a Man Out of His Senses for a Day”)中写道,他调制出一种类似“飞天药膏”的膏剂,试着涂在室友身上,结果让他乐不可支,而室友们则惊恐万状。
从阿普列乌斯到巴勒斯,西方文学中对变形的描述比比皆是,至少对于本人吸毒或让他们笔下的人物吸毒的作家是如此。因而,蜥蜴男孩、巴勒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其他性嵌合体人物以及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笔下和母鲨交配的马尔多罗(Maldoror),都是《金驴记》里猫头鹰女人潘菲乐的后裔。如果说巴勒斯确实沿袭了动物变形这一文学传统(萨满教义和古代神话昭示我们,这种传统比《金驴记》要早几千年),那么他1959年出版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则彻底背离了这个传统。该书标新立异,首次运用了现在广为人知的“剪裁手法”,不同的文本被糅合在一起,还有些文本被剪裁成片段,重新组合。20世纪初,达达主义诗人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就开始了名副其实的文本剪裁,但巴勒斯宣称,他的实验性写作技巧直接源自艺术家布莱恩·吉森(BrionGysin)的影响。并不是所有同时代作家都赞成这种激进的创作手法;巴勒斯自己曾经提到,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就曾表示反对,称其更像是在安装下水管道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对巴勒斯来说,剪裁是一种反叛行为,部分是为了抗拒由书写的文字结构强加的极权态势。如同某种文学界的弗兰肯斯坦博士(抑或更确切地说,是由巴勒斯本人创造的本维博士,他象征着医学的无能为力和对病人最为严苛的“照顾”),巴勒斯先将文本劈成碎片,再用这些碎片合成新的组合体,并企图在组合体内注入生命。巴勒斯说,书名受了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启发,“含义即文字的字面意思:裸体午餐——一个凝固的时刻,每个人看着叉子上叉着的东西”。他说“意识即裁剪”,他的意思是,将该创作手法运用到写作中能够更好地在作品中表现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我们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市,无意中听到只言片语,没有前文,也没有后续;跳过一个个电视频道,无数毫无关联的节目无序地在屏幕上闪过;我们遐想的时候,大脑掠过一个又一个不相关的思维对象。
当精神药物进入人体,意识的多变属性更突出地表现出来。此类药品会改变使用者的意识状态,尤其是致幻剂,它能使人的自我意识和时空感发生巨大变化。不仅会出现幻视,也会出现幻听和味觉、嗅觉、触觉失调。在药物作用下,生命的断裂感会更加明显——感觉失调、异常兴奋、妄想、恐慌、延展的景象、与活在内心的生命的互动,这可能导致和正常清醒状态下反差巨大的体验。
本作品集本质上也有剪裁元素,编者或编辑决定剪哪里和贴到哪里。在同一个主题下,作家们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场景——有些经历是旁观者讲述的,而有些则是亲身经历,有些冷静,有些狂躁,罪恶感或任性放纵遭遇冰冷的黑色幽默。那么,本作品集也是一个嵌合体,由不同的文本和不同世界的经历及想象嵌合而成。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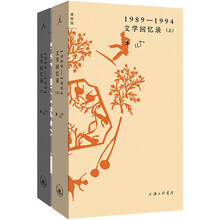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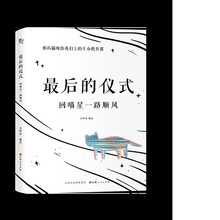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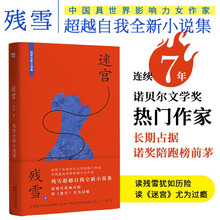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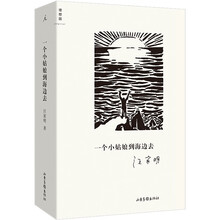


——Scene
这部文集提出药物使我们超然于理性之外,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或许能发现、探索某种奥义;我们可以从*癫狂的梦幻中汲取真知,以此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会。
——《格拉斯哥先驱报》
理查德·罗吉利流畅的行文表明,如果依赖比茶和香烟更令人兴奋的东西,他是无法编着出这样一部文集的。他既有学者风范也有人文情怀;他似乎对迷醉剂了如指掌,但绝不会改信毒宗;他站在真理一方。
——《每日电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