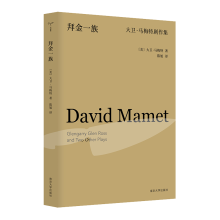我画昆曲《义侠记·戏叔》,友人戏评:“金莲不够妖媚,二郎过于凶恶。”
金莲浪荡妖媚,二郎正义凛然——此人心之所议,却未必写在脸上。我读大学时,高年级有一“院花”,长得冰清玉洁,活生生童话里的白雪公主。近者却皆知其人城府颇深,谓伊水性杨花似嫌过之,但每弄异性于股掌之间,必达其目的乃后已。相反,有的人面貌丑陋,却心地善良;有的人魁梧壮硕,却细致温存。人不可貌相,知人知面不知心,此之谓也。
当然,相由心生,人“面”合一的情况也同样比比皆是。终归是真的假不了,假的难成真。然而混淆真伪、颠倒心相正成为当世人心之恶疾。现代人思路开放无际,喜欢翻案,好作怪论奇谈,以为不同凡响。所以,人们开始同情潘金莲了,武松显得不解风情了,各地政府争抢起西门庆的故里了,武大那种窝囊废不但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早该自绝于人民了。
传统成为时尚的靶子,艺术价值观让位于“开放的文本”,是为“多元化”。
所以,戏剧终不能契合时人口味,并非其节奏太慢,而是它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刻板而过时,不够开放和多元。红氍毹上,无论是小金宝饰演的潘金莲,还是朱传茗饰演的潘金莲,无非是扮相、唱腔和做派稍有不同而已,潘金莲始终是那个被视作“反面角色”的潘金莲。可到了银幕前、荧屏里,影视剧里的潘金莲真是个个青春曼妙,惹人怜爱,观众心疼无已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金莲固然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孔子尚且号称未曾见过“好德如好色”之人,谁个不想满眼里郎才女貌,金童玉女!可她勾引自己的小叔子则不但千错万错,且真是岂有此理。那武松纵然识得风情美貌,又焉能与嫂子苟且?此其一。其二,纵得西门大官人倾心,央求武大写就一纸休书罢了,如此只落得个负心之恶名,总不至于沦为毒妇,心生歹意,谋杀亲夫,走上不归之途。
毒妇罪不能免,荡妇又岂能轻饶?试看,那金莲百般“戏叔”未遂,不禁欲火难浇,搭肩递盏,投怀送抱。二郎怒火中烧,大喝声“呀呸”,便唱道:
(生)【扑灯蛾】我怪伊忒丧心,怪伊忒丧心,羞耻全不怕!有眼睁开看,把武二特地详察也!
(贴)啐!啐!
(生)走来!我是含牙戴发顶天立地丈夫家,怎肯做败伦伤化?
“丧心”二字,正是一语中的。人既已丧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面的结局也就在情理之中,可想而知了。金莲的人生固然是极大的悲剧和不幸,武大又何尝不是?为金莲翻案之流,虽未必丧心,已可见必是传统道德意识淡漠,不知何为“败伦伤化”者也。
……
展开